- 0
- 0
- 0
分享
- 《戏剧》2022年第3期丨李言实,董潇:贝克特戏剧听觉叙事研究
-
原创 2022-08-03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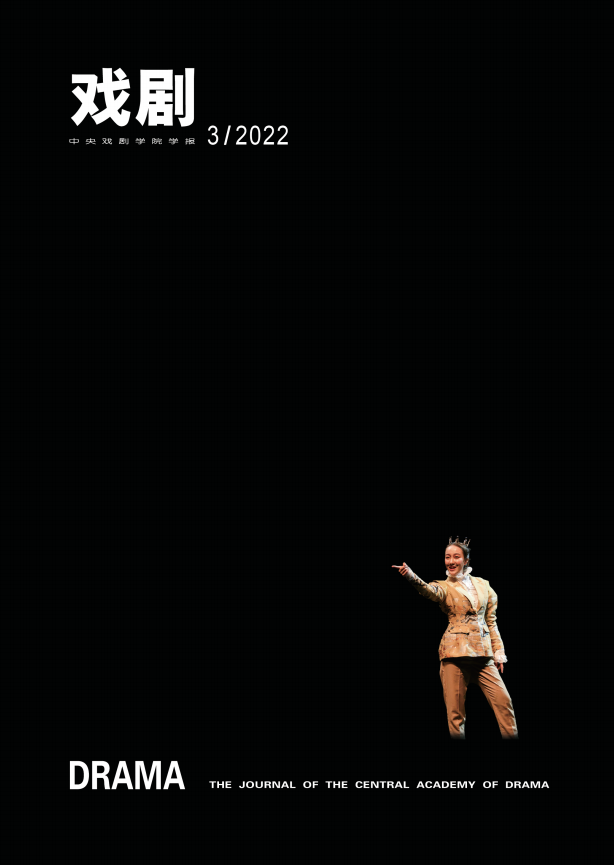
李言实
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董潇
山西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助教
内容提要丨Abstract
贝克特戏剧表现出跨媒介叙事的特点,其中听觉叙事尤为突出。本文从人声叙事、物声叙事、无声叙事和音乐叙事等方面对贝克特戏剧中的听觉叙事进行研究,试图探索贝克特如何用听觉叙事来解构人物、语言、戏剧,乃至叙事本身,引导西方戏剧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从戏剧剧场走向后戏剧剧场。本研究在扩展贝克特戏剧研究内容,丰富贝克特戏剧研究方法的同时,还试图探索一条将听觉叙事应用于戏剧研究的可能的路径。
Beckett’s drama presents the features of multi-medial narration, of which acoustic narration is highlight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acoustic narration of Beckett’s drama from four aspects, i.e. the character’s voice narration, the objects’ sound narration, the silent and still narration, and musical narration, with the aim to explore how Beckett used acoustic narration to deconstruct the character, language, drama and even the narration itself, leading the western theatre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from dramatic theatre to post-dramatic theatre.
关键词丨Keywords
贝克特 戏剧 听觉叙事 声音 沉默 音乐
Beckett, drama, acoustic narrative, sound, silence, music
从其早期和后期作品比较来看,贝克特戏剧表现出从戏剧文本向戏剧剧场的转变。贝克特前期戏剧作品文本性较强,主要通过人物的对话表现世界与人生的无望、衰败、荒芜和虚空;其后期作品剧场性越来越得以加强—悬置文本,去掉人物,突出灯光、声音等跨媒介手段的使用。与其相一致的是,其戏剧形式也逐渐从舞台向其他媒介方式转变。与冲击性极强的视觉叙事相比,贝克特戏剧中的听觉叙事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作为后经典叙事学一个最新发展的分支,听觉叙事源自于跨媒介叙事和声音研究,意在探索不同媒介中的声音、音乐与叙事的结合,回答声音如何支撑叙事结构,甚至它们自身如何承担叙事功能等问题。“听觉转向”最早发生于文化研究领域。1960年,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埃德蒙德·卡朋特(Edmund Carpenter)在其主编的《传播探索》(Exploration of Communication)中批评了西方文化中的视听失衡现象,指出需要建立与“视觉空间”感受相异的“听觉空间”(acoustic space);1977年,同为加拿大学者的雷蒙德·莫里·谢弗(Reymond Murray Schafer)的《为世界调音》(The Tuning of the World)为听觉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00 年以后,听觉研究开始进入人文学科。听觉叙事最早由加拿大学者梅尔巴·卡迪-基恩(Merba Kardi-Kean)于2011年提出,他对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进行了听觉感知叙事研究。2014 年德国帕德博恩大学召开的会议“听觉叙事学:声音与叙事的结合”(Audionarratology: The Interfaces of Sound and Narrative)首次提出“听觉叙事学”这一概念。由贾米拉·米尔多夫和迪尔·肯泽尔(Jarmila Mildorf &Till Kinzel)主编的同名论文集于2016年由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
在国内,听觉研究首先兴起于文化文学领域。王敦《声音的风景:国外文化研究的新视野》(2011年)介绍了文化研究中的听觉问题;周志强《声音与听觉中心主义—三种声音景观的文化政治》(2017年)讨论了声音文化政治的编码方式与生产机制;曾军《转向听觉文化》(2018年)提出了“听觉转向”应该思考的几个问题。将听觉研究与叙事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第一人是傅修延教授,他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的《听觉叙事初探》创建了听觉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工具。之后,傅晓玲在2014年将其和翻译研究相结合,试图建构翻译学的听觉叙事翻译策略;刘亚律在2016年讨论了听觉叙事的多重维度和意义;周志高在2018年提出了听觉叙事的研究范式。在文学领域,目前听觉叙事主要应用于小说研究。杨志平在2017年分析了《红楼梦》中的听觉叙事;吴晓丽在2020年讨论了卡森·麦卡勒斯小说中的声音叙事。
贝克特说过,“我的作品是关于基本声音的问题,尽可能完全的声音,我只为这一点负责。”[1](P63)贝克特对语言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在其剧作中,贝克特使用了多种听觉叙事手段,包括人声叙事、物声叙事、沉默叙事和音乐叙事,以这些手段来质疑语言、否定语言,直至最后消解语言,从他的第一部剧作《等待戈多》开始,声音、沉默、音乐在贝克特的戏剧叙事中就占有重要的地位。《不是我》中的那张嘴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讲述了一个“她”的故事;《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中以机器为媒介的过去的声音和现在发出的苍老的人的声音形成鲜明的对比;《脚步声》中“能够清楚地听见有节奏的脚步声”[2](P277)构成本剧的听觉叙事空间;《跌倒的人》中乡间的绵羊和鸟儿的叫声、卡车声和自行车铃声等一起建构起一道独特的爱尔兰声音景观;在语言停止的地方,沉默便出现,从其早期作品《等待戈多》到中期作品《美好的日子》 再到其后期作品《那时》,沉默和停顿起到改变叙事节奏、表现思想停顿、给读者和观众留白的作用;当声音和沉默都不能充分表达他对语言的怀疑和否定时,贝克特用音乐叙事取代了语言,语言和图像成为音乐的注解。贝克特在戏剧中使用多种听觉叙事手段,包括人声叙事、物声叙事、无声叙事和音乐叙事等,他用分裂的、碎片化的人声叙事来表现语言的不可靠性,用操控人物的物声叙事来表现人的无能、无知和无力,用沉默和音乐来表现世界的不可言说性。
一、不可靠的叙事者:贝克特戏剧中的人声叙事
贝克特表现的是人的无能、无知、无力,他的人物通常都是分裂的、碎片化的。随着对自我的探寻越来越深入,贝克特的戏剧人物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我分离和断裂感,他们不但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分离,他们的肉体自我与精神自我也处于隔绝状态,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儿,要做什么,他们试图通过与别人或另一个我对话去找寻自我,然而结果总是失望。贝克特戏剧呈递减式发展,剧中的人物越来越少,直至成为碎片化的某个身体部位,这种碎片化的身体探寻自我的方式是回忆或与自己的对话,随着探寻的深入,这种分裂感越来越强,由一个分裂为模糊的两个,再到明确的两个,最后可能分裂为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自我。这种与自我的对话往往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表现出极大的不可靠性。
《不是我》中只有一张嘴向黑暗中的“听者”倾诉一个“不是我”的故事—“……出来……进入这个世界……极小的小女孩……发现自己置身于黑暗之中……发不出声音……整个身体都像是消失了……没有爱……沉默不语了一辈子……突然来了冲动要……讲述……开始让它倾泻而出……一连串的话……没谁能明白……如此这番……继续……”,她似乎在努力讲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所遭受的一切,但是讲述中又似乎在回应听者的质疑,“……什么?……谁?……不!……她!”。[2](243-256)她刻意以“她”为叙事人称,好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极力使读者/观众相信这是“她”的故事,但在她反复强调“不是我,是她!”的过程中,读者/观众开始质疑她的叙事的真实性。
《那一回》中人物分裂为三个自我,舞台上只有一张“年老苍白的面孔”,仅做“眼睛开合”的动作,头的上方和两边传来A、B、C三种声音,分别交替讲述童年、青年、老年三个人生阶段的回忆,“它们以寻常的语速反复不停地变换嗓音”,三种声音“合成一股声音流,前后调整而不中断”。他回忆了小时候去码头的一段经历、青年时的一段爱情和老年时一次躲雨的经历,但是每一个声音都在讲这是“你为排解空虚不断地编造出来的故事”,每一个声音对于回忆都持怀疑的态度,“那是另外一回吗所有那一切都是另外一回吗除了那一回还曾有过另外一回吗”。[2](PP259-273)叙事的声音相互补充又互相矛盾,每一个声音都讲述一段故事但是又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表现出叙事的极大的不可靠性。
贝克特的戏剧没有戏剧性,去掉了动作性,只有碎片化的某个身体部位通过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以戏剧独白形式表现的“回忆剧”。在努宁(Vera Nünning)看来,这种“回忆剧”有着突出的叙事特征,通常是一个角色讲述自己生命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它是一种“结合了诗意的用词、戏剧的表现形式和讲故事的元素构成的戏剧独白,通常都意味着一个不可靠的第一人称的叙事者”。[3](P266)这个叙事者之所以不可靠,是因为他/她不仅重述故事,也会“生成”叙事,在回忆中,他/她“生成”了一个虚构的世界,理查兹(Brian Richardson)称之为“生成的叙事者”(generative narrator)[4](P685)。究其原因,或是不愿面对自己所受的创伤,或是因年老或精神疾患不能分清事实和虚构、真相和谎言。贝克特以不可靠的叙事者讲述的不可靠的叙事,表现了对人的怀疑、对语言的怀疑,以及对历史的怀疑。
二、被操控的叙事者:贝克特戏剧中的物声叙事
除了人的声音,贝克特还充分使用物体的声音,在执导《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时,贝克特指出,“声音要尽可能地多,从头到尾都要有物体的声音。”[5](P24)在不可靠的人物叙事之外,贝克特还使用不同的生物或物体的声音进行叙事,这些物声叙事本身就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或者构成一定的“声音景观”,为戏剧的推进构建一个叙事空间,或者成为叙事的操控者,控制着人物叙事的开始和结束。为对抗当代文化中视觉对听觉的压迫,加拿大社会学者夏弗(R. M. Schafer)在其《音景:我们的声音环境以及为世界调音》一书中提出“声音景观”(soundscape)这一概念,简称音景,与强调视觉的图景(landscape)一词相对应。按照夏弗的定义,声学意义上的音景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主调音(keynote sound),相当于背景声音;二是信号音(signal sound),类似于前景声音;三是标志音(soundmark),与地标(landmark)一词相对应,它标志一个地方的声音特征。[6](P225)
贝克特将他对存在的感觉完美地融合在广播剧这种声音的艺术形式中,约翰·皮林(John Pilling)认为贝克特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是脱离肉体的声音,尤其是那种可以激发人们想象力的声音。《跌倒的人》是贝克特创作的一部广播剧,其中听觉元素特别突出。一开始就用“乡下的各种声音”营造出乡村音景,其中“绵羊、鸟、奶牛、公鸡”的叫声,“自行车的铃声”“机动货车的声音”等是处于叙事最深层次的声音,属于“标志音”,标志出独特的爱尔兰乡村的声音特征;处于中间层次、作为叙事背景声音的是路旁农舍中传出的《死神与少女》的“微弱的音乐声”,在这一“主调音”中,鲁尼夫人“踟蹰而行的脚步声”以及反复出现的“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就被前景化,成为叙事的“信号音”。这一信号音从头贯穿至尾,并在鲁尼夫人和鲁尼先生谈论第二天的布道词时得到反讽,“上帝要提携跌倒的人,又扶持被重担所压的人。”[2](PP5-57)他们并没有得到提携,也没有得到扶持,在剧的开头听众得知他们失去了女儿小米妮,在剧的结尾,听众又听到一个小孩倒在车轮下死去,背景音乐《死神与少女》再次响起,与开始时的音乐形成呼应,以此主调音表现了该剧的悲剧主题。
贝克特戏剧中的物声不仅构成叙事音景的不同层次,对叙事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其本身还承担着叙事功能,起到操控叙事者的作用,主宰人物叙事的开始和结束,凸显人物的被动和面对命运的无奈,更进一步,物声还参与到叙事之中,在语言之外物声本身成为叙事者。《俄亥俄即兴》中只有两个角色—听者(L)和读者(R),剧作以“敲桌”声开始,似乎在催促R继续他的讲述,在敲桌声的促使下,R开始了讲述,“几乎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但是听者似乎对此很不满意,他“左手敲桌”,R只能继续讲述。每当他想要中断讲述或者跳过某一段内容时,都会有敲桌声制止他或催促他继续讲下去,直至最后他合上书。[2](P352)在这里,叙事者失去了其主动性,成为被操控的叙事者。这种操控叙事进程的声音在《歌词与音乐》和《卡斯康多》甚至有了名字,成为剧中的一个角色,参与到叙事之中。《歌词与音乐》中柯罗克用“棍子重重的敲击声”控制歌词和音乐,命令他们今夜的主题是“爱”,而且要求他们“大声点儿”,最后在歌词和音乐唱出关于爱情的歌时,我们只听到“棍子落下的声音”和“渐渐消失”的“趿拉着拖鞋走路的声音”。[2](P112)《渐弱》中的“开启者”也是随心所欲控制“人声”和“音乐”的角色,它可以随意打开或关上人声的讲述和音乐的起止,直至最后看到人声和音乐达成一致。在这两部剧作中,语言受到物声的操控,贝克特用声音消解了语言。
三、无声的力量:贝克特戏剧中的无声叙事
音景不仅由各种声音构成,也包括无声,傅修延教授指出,“无声也是一种音景”,无声与有声具有“同等的地位”。[6](PP146-147)在音乐中,无声与音乐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加拿大作曲家约翰·韦恩茨威格(John Weizweig)在其《无言》中用一段很长的停顿来纪念纳粹暴行的牺牲者;美国音乐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的《4分33秒》就是一首完全无声的乐曲。在传统戏剧中,语言及其发出的声音一直被用来作为表达思想和交流的工具,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可憎,“上帝已死”,信仰崩塌,人们开始怀疑语言承载意义的功用,语言失去了它的价值。贝克特对语言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和日常交流的工具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因此,他的戏剧中出现大量的停顿和沉默,仅在《等待戈多》一剧中,沉默就出现 115 次。苏珊·桑塔格认为,在沉默的几种运用方法中,它首先可以用来“证实思想的缺席或弃权”,这一点运用于压制性的社会关系中。这一点在《等待戈多》中幸运儿的失语体现最为突出—他是一个被奴役者,也是一个“思考”的表演者。第一幕中幸运儿还可以用碎片化的语言来表演“思考”,以揭露理性的失败和反抗强权;第二幕时他的声音已经被剥夺,压迫者失明了,被压迫者沉默了,被压迫者再也不能发出有声的抗议,压迫者再也看不到他的臣民所遭受的困境。在贝克特看来,语言和沉默是一个镜子的两面,当语言失败的时候,沉默就出现了。贝克特认为,“《等待戈多》像一艘沉船,而沉默就像涌进的海水,时刻都有可能使这艘船倾覆。”[7](P xiii-xiv)实际上,这部剧可以被看作语言与沉默、意义与无意义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出现在人物对话之中和对话结束的大量的停顿和沉默,表现了人与人的疏离和隔膜以及生存的无意义。沉默揭露了语言的贫瘠,也反映出人的存在的困境。贝克特的沉默和凯奇的《4分33秒》一样,用沉默来对抗语言,用沉默来消解语言。
在人声的沉默之外,声音的静寂在贝克特戏剧声音叙事中也有重要作用。罗伯特·威尔逊有一句著名的宣言,语言是想象的障碍,因此,静默成为威尔逊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威尔逊制作的《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中,开场就是长达20分钟的静寂,年老的克拉普以非常慢的节奏剥香蕉吃香蕉,威尔逊用几近于静止的流动的慢动作,一方面表现了克拉普的年迈,另一方面拉长了物理时间,扩大了回忆空间。除了开场的静默,演出过程中也有大段大段的静寂。在贝克特和威尔逊这里,静寂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像凯奇的《4分33秒》一样,是声音的静默。在静默中,时光在流逝,克拉普在一步步走向衰老和死亡,他知道,“白日已尽,黑夜将临……”。[2](P78)此剧中的声音同样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与静寂形成强烈的反差,构成对立的统一。在20分钟的静默后,突然响起的一声炸雷,让观众的身体、同时也让灵魂震颤。随后是持续的不停歇的雨声、录音带掉到地上的巨大轰响、被放大了的录音带空转的吱吱声、克拉普黑暗中拔出酒瓶塞子和塞住酒瓶的声音,这些外部声音,把克拉普的内心反衬得更为孤独。雷雨声停歇之后,人声出场—当他听到回忆中的恋情时,碟带里传出年轻的克拉普的温暖而亲切的声音,与现在年老的、冰冷的、金属般的声音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舞台上的克拉普时不时发出尖叫,因为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一切;当他把又一根香蕉塞入口中,双手举起,瞪大眼睛时,观众等待着他像开头那样刺破静默的尖叫声时,他大张着嘴,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舞台上唯有一片静默。这无声的尖叫,正如那震耳欲聋的雷雨声,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贝克特人物那可笑可悲、荒诞荒谬的无奈和寂寥。在威尔逊制作的贝克特剧中,过去与现在、自然与技术、声音与静默、贝克特的文本与威尔逊的舞台同时并存,将一个不可接近的、孤独的、脆弱的克拉普呈现在观众面前。
沉默和静寂是贝克特戏剧中无声叙事的主要元素,这里的无声是对语言和声音的反抗,它具有比有声更强大的力量。沉默是另一种方式的言说,静寂也是声音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它们与语言和声音构成对话,以一种观众听不见的方式参与到叙事之中。贝克特认为,在沉默与语言的斗争中,语言注定失败,最终是沉默,这样语言就可以“失败得更好”;但是正是沉默与语言的斗争使得人类更接近真理,也构建了一种新的观看和倾听的方式。
四、拟人化的音乐叙事:贝克特戏剧中的音乐叙事
与语言相比,音乐是一种不同的沟通方式,它比语言更为直观,可以将意义直接转递给听者。瓦格纳也认为音乐具有超验和属于彼岸世界的潜能,即它是形而上的,它更适合于用来表达抽象的思想。[8](P105)因此许多作家试图跳出语言的束缚,或通过给词语和文本形式加上声音效果来传达抽象的思想。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9](P189)但是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西方世界物质和精神都崩塌的贝克特来说,存在是荒诞的,生命是虚空的,面对这种荒诞和虚空,没有什么可表达的,也没有什么能够表达这种无以表达的东西。贝克特转向音乐,寻求一种新的表达的可能。
贝克特开始在剧作中探讨词语与音乐的关系,在《歌词与音乐》中,他将词语和音乐设定为两个角色,他们在讨论今夜的主题—爱。词语“洪亮地”说道,“在所有的激情当中,怠惰是最为强烈的激情……”,[2](P111)但是音乐似乎对此不满,他用指挥棒重重地敲,即使词语抗议抱怨也无济于事。当词语继续说出关于爱情的话语时,音乐不断对此做出改进或给出建议,直到词语说出令人满意的话语时,音乐才邀请词语加入并进行伴奏。在这个过程中,音乐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它引导、修正、改进、接受词语,直至最后词语完全服从。
语言在与音乐的决斗中败下阵来,因此在贝克特的其他剧作中,往往是音乐,而不是与之相悖的语言揭示作品的主题和真正意义。《美好的日子》中,温妮对丈夫威利诉说着过去美好日子的回忆,但是威利只是偶尔漫不经心地回应一下,最后威利终于从洞穴里爬出来向温妮爬去,温妮高兴地哼唱起歌曲,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唱的是《快乐的寡妇》。在《跌倒的人》中,鲁尼夫人去接视力不好的丈夫下班,她遇到一切貌似热闹的景象都被剧中开头和结尾的音乐无情地揭示,背景音乐是舒伯特的歌曲《死神与少女》。音乐表现了现实的无情—他们的女儿不幸夭折;泰勒先生的女儿被摘除了子宫;斯洛克姆先生的车压死了一只母鸡;菲特小姐的母亲乘坐的火车出轨了;一个小男孩因为捡球被火车压死了。贝克特以音乐叙事表现了丈夫的在场性的缺席和并没有得到拯救的跌倒的人,进一步凸显世界的荒诞和生命的虚空。
贝克特在音乐叙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最后完全抛弃了语言,只用图像和音乐进行叙事,视觉与听觉叙事交相呼应,一起形成复调叙事。如他的后期作品《夜与梦》就是以舒伯特的同名音乐作品命名,是一部完全抛弃了语言,只用图像和音乐叙事的戏剧作品,整部剧作没有对话,只是列出的十几条舞台说明。贝克特在“要素”说明中就明确指出,其音乐是“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夜与梦》的最后七节”。剧中男子哼唱着《夜与梦》的最后七节,“回来吧,圣洁的夜;回来吧,甜美的梦……”,随着灯光暗下,他唱着最后三节“甜美的梦啊……”[2](PP369-370)陷入梦境。伴着歌曲的反复吟唱,梦境与现实交替出现,使人分不清梦与现实。贝克特用图像和音乐诉诸与视觉和听觉的感受,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对夜与梦的渴望,因为只有夜与梦才能带给人些许的温暖和慰藉。
结语
随着对语言的抛弃和对视觉听觉叙事的倚重,贝克特后期戏剧作品越来越走向抽象和虚空。他的《呼吸》没有角色,没有语言,叙事元素只有灯光和声音,仅持续35秒。随着灯光亮起,出现在舞台上的是一堆垃圾,紧接着一声“微弱而短暂的哭声”是吸气的声音,然后沉默,之后是呼气的声音,紧接着是“如前的哭声”,然后沉默。[2](P237)贝克特以声音和沉默与语言和意义抗争,以表现无以表现的一切,正如他所说:“没什么可表达的,没有表达的手段,没有表达的内容,没有表达的力量,没有表达的欲望,也没有表达的责任。”[10]
贝克特对于戏剧视觉和听觉的追求与其对文本的精确性的追求是一致的,通过对每一个细节的把握达到对戏剧主题的完美呈现。从用语言消解语言,到用声音消解语言,再到用沉默消解语言,直至用音乐消解语言,贝克特用听觉叙事彻底完成了语言的消解,在这一过程中,贝克特解构了语言、解构了人物、解构了戏剧,乃至解构了叙事本身,从文本走向剧场,从舞台走向其他媒介,从戏剧走向后戏剧。
参考文献
[1]BECKETT Samuel. Disjecta: Miscellaneous Writing and a Dramatic Fragment[M].London: John Calder, 1983.
[2]塞缪尔·贝克特. 短剧集(上)[M]// 刘爱英,等译. 贝克特全集(22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
[3]NüNNING Vera ed.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Trustworthiness: Intermedi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M].Berlin: De Gruyter, 2015.
[4]RICHARDSON Brian. Voice and Narration in Postmodern Drama[J].New Literary History ,2001(32.3).
[5]LEVY Shion. Samuel Beckett’s Self-Referential Drama[M].London: MacMillan, 1990.
[6]傅修延. 听觉叙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7]BECKETT Samuel. The Theatrical Notebooks of Samuel Beckett: Waiting for Godot[M]. MCMILLAN D. , KNOWLSON J. eds.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93.
[8]WAGNER Richard. Beethoven(3rd ed.)[M]. DANNREUTHER Edward , trans. London: New Temple Press, 1903.
[9]HEIDEGGER Martin. Basic Writings,Letter on Humanism[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10]LEZARD Nicholas. Conversations with Samuel Beckett and Bram van Velde by Charles Juliet[N].The Guardian, 2010-01-23.
学报简介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影视学术期刊,1956年6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戏剧学习》,为院内学报,主编欧阳予倩。1978年复刊,1981年起开始海内外公开发行,1986年更名为《戏剧》,2013年起由季刊改版为双月刊。
《戏剧》被多个国家级学术评价体系确定为艺术类核心期刊:长期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5年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成为该评价体系建立后首期唯一入选的戏剧类期刊。现已成为中国戏剧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同时作为中国戏剧影视学术期刊,在海外的学术界影响力也日渐扩大。
《戏剧》旨在促进中国戏剧影视艺术专业教学、科研和实践的发展和创新,注重学术研究紧密联系艺术实践,重视戏剧影视理论研究,鼓励学术争鸣,并为专业戏剧影视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的信息和资料。重视稿件的学术质量,提倡宽阔的学术视野、交叉学科研究和学术创新。
投稿须知
《戏剧》是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影视艺术类学术期刊。本刊试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作者来稿须标明以下几点:
1.作者简介: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学位。
2.基金项目(文章产出的资助背景):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
3.中文摘要:直接摘录文章中核心语句写成,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篇幅为150-200字。
4.英文摘要:与中文摘要大致对应,长度为80个英文单词左右。
5.中文关键词:选取3-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
6.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大体对应。
7.注释:用于对文章正文作补充论说的文字,采用页下注的形式,注号用“①、②、③……”
8.参考文献:用于说明引文的出处,采用文末注的形式。
(1)注号:用“[1]、[2]、[3]……”凡出处相同的参考文献,第一 次出现时依 顺序用注号,以后再出现时,一直用这个号,并在注号后用圆 括号()标出页码。对于只引用一次的参考文献,页码同样标在注号之后。文末依次排列参考文 献时不再标示页码。
(2)注项(下列各类参考文献的所有注项不可缺省):
a.专著:[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c.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M].
论文集主要责任者.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d.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e.外文版专著、期刊、论文集、报纸等:用原文标注各注项,作者姓在前,名在后,之间用逗号隔开,字母全部大写。书名、刊名用黑体。尽量避免中文与外文混用。
来稿通常不超过10000字。请在来稿上标明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及电话,发送至学报社电子信箱:xuebao@zhongxi.cn。打印稿须附电子文本光盘。请勿一稿多投,来稿3个月内未收到本刊录用或修改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发现有一稿多投或剽窃现象,对我刊造成损失,我刊将在3年内不再接受该作者的投稿。来稿一般不退,也不奉告评审意见,请作者务必自留底稿。
《戏剧》不向作者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也未单独开设任何形式的网页、网站。同时,中央戏剧学院官微上将选登已刊发文章。
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
图文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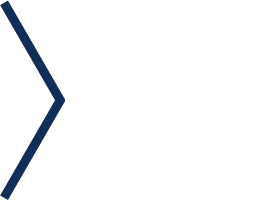


欢迎各位校友、社会各界人士关注中央戏剧学院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 “zhongxi_1938”,或扫描上方二维码进行关注。
网站:http://www.chntheatre.edu.cn/
-
阅读原文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数艺网立场转载须知
- 本文内容由数艺网收录采集自微信公众号中央戏剧学院 ,并经数艺网进行了排版优化。转载此文章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标注“作者”、“来源:数艺网” 并附上本页链接: 如您不希望被数艺网所收录,感觉到侵犯到了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数艺网,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及时处理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