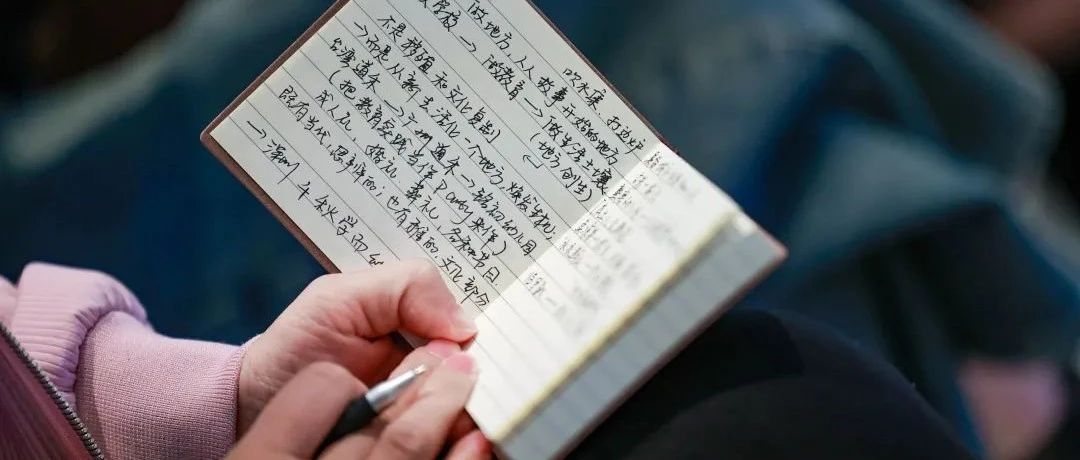- 0
- 0
- 0
分享
- 杨国辛:谋心
-
2023-09-07

杨国辛近照
杨国辛的作品经历过多次转变,从带有政治批判意义和消费景观的表达,到文化景观的内在情境,如今的画面表达又重新回到历史和现实的范畴,实际上,现实主义的观察方式一直贯穿其中。
在这些最新的画面中,杨国辛记录下了他的思考和无法言语的感受,世界在当中被看为了一个整体,此地与彼地,此时和彼时构成的因果关系不断地形成效应,在打边炉的采访当中,杨国辛提醒道,任何一个个体都不能独善其身,作为艺术家,脱离当下的现实语境去谈艺术,或将艺术视为现世的生存手段,不过虚无。如此,还不如当一名“隐者”,游手好闲,在喧嚣当中独自谋心。


跳出现实,从高处观看
ARTDBL:请谈谈展览“一个隐者的时间之书”里的这些“日记体”绘画,你是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之下创作了这批作品?
杨国辛:这批作品的形态是偶然形成的。2020年初在武汉,大疫封城,被困在汉口老家,近五个月的时间,哪里也去不了,真正是足不出户。日子被沉重悲哀的心情笼罩。带在手边的两本笔记本和一些工业装裱的扇面形宣纸,成了打发心境的载体。在那么小的一个纸张范围里,我每天用丙烯和墨在上面乱涂乱画,无意中使每天的所思所想所见有了记录,随后的三年里因照顾年迈的父母,我经常往返于广州和武汉之间,疫情起起伏伏,不时的封控,无处不在的检测,没完没了。余时依旧胡写乱画,仿佛已经成了习惯,从2020年一直延续下来。这批作品与我常态的创作不太一样,看起来思绪很乱,也很散,在画里写的一些文字,不满意就随地涂抹掉了,也不考虑构图是否得当,所以李邦耀老师才说,这批作品是一种日记体绘画。
疫情很不平常,而它的影响也一直在延续。没法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我避开眼下,去画抽象的形式感,去探讨某些艺术问题,很不现实,也很滑稽。思考眼前的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记录下来这些具有影响的点点滴滴,一笔一笔记录下来这些跌宕起伏的动荡,在画面上清晰地保留我的记忆、时间和思维的痕迹。
ARTDBL:你所画的不仅是身边的事,大量的事件和图像记载了历史和现实的沉重,它们因何会引起身在此地的你的注意?
杨国辛:这些作品涉及到了广泛的历史事件、艺术、战争、自然灾害、风光、文化名人等等,在我看来,一切都是有联系的,当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和此地在我眼下所发生的事情,都存在着因果关系,事情都不是孤立的。只是有些事情及时反映在了我的思考里,有时候却是一种无可奈何、无法言语的感受。2020年,武汉封了城,但那并不是武汉的事情,全世界都拉了闸。最近日本倒下核废水,我也并不把事件和舆论孤立地看待。大海是连在一起的,不是日本的海,也不是中国的海,也不是美国的海,海洋是全人类的。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到底是科学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往深处想的时候,常常使人迷茫。
我使用的图像都有依据的,有时候直接来自网络,对于一些事件的记录,我并没有只选择甲方或者乙方。瓦格纳的老普死之前,我画了他的战士们,年轻的士兵们虽然很酷,但还是炮灰,酷酷的炮灰。在网上看到一些俄乌战争的视频,有些视频来自战场上装在钢盔上的摄像机,边打边拍,简直就像直播卖货一样。我看到俄罗斯士兵和乌克兰士兵的死状,心里很难过。都是年轻的生命,为什么要撕杀在战场?据媒体报道,士兵在现代战争的战场上,生存率平均只有2.5天!俄罗斯的那些母亲们在莫斯科游行抗议,是人都会理解的,哪个母亲不惦记着儿女,何况一个活生生的儿子死在战场上?
在展览现场,这些不同类型的画面被相互穿插和关联起来,与战争有关的图像里穿插着文艺复兴时期静谧的女性图像,国际事件里穿插着摇滚乐队和交响乐团的演奏,喧闹的事件当中穿插着花花草草,事实上,我也是这么穿插着画的。文艺复兴将人性从神性当中解放了出来,那么文艺复兴所张扬的人性是什么?冲破了什么?对后来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可以在现实的思考中,感受得到那些语言、具体的色彩和造型用光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人性的解放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花花草草能让我的内心稍稍平复一些,音乐、绘画和自然都是人间的美好,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调节,像是心境的调整,也能够让我跳出现实,从高处观看。
ARTDBL:像2020年的武汉,今天的核废水,也都有所谓主流和正确的叙事,它们为什么没有进入到你的系统当中?你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
杨国辛:主流话语有主流的内在诉求,作为个体,切身感受才是最真切的,某种意义上,有些诉求与我个人没有多大的关系。我看问题的角度,只与我的切身感受、我的切肤之痛相关。当时打边炉向我邀稿,我用了四个小时就写完了《沉沦》这篇文章。
在我看来,当时惶恐的情境中,作家方方讲的一句话分外震动我,她说“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体身上就是一座大山。”我当时在武汉,每天早上5点多起来就看方方最新发布的日记,她写的人和事,和我在院子里接触和观察到的人和事,是可以引起共鸣的,我认为方大姐写得还是比较克制的,写得很温和,也很有分寸,但是她的下场居然是沦为了众矢之的。疫情之后的社会,分化更为严重,很多人干脆就不说话了,稍微说一句,也总有一些人带节奏、带情绪,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我真的不明白了,唯有失望。
ARTDBL:你对于真实外部世界的态度和立场,都直接表现在这些画面中吗?
杨国辛:如果涉及到具体的问题,比如战争,我的态度就是厌恶一切战争,战争就是绞肉机,残酷地夺走无数的生命。历史告诉我们,战争是野心家的工具。我曾从不同的角度画了被炸毁的乌克兰马里乌波尔歌剧院,这不就是战争所带来的吗?战争毫不考虑这栋建筑的艺术性和历史性,在战争面前,不仅是人的生命,文化也是脆弱的。1980年代,我曾在平山郁夫的画册里看见过他用日本画的方式来表现丝绸之路上的巴米扬大佛,塔利班用炮轰毁了大佛以后,我很是震惊。我再来画巴米扬大佛的时候,写上了祖元禅师的一句偈语“电光影里斩春风”,我要说的是,杀戮对文化没有用,不过是像用刀在春风里划了一刀。
现实难以改变,很多问题也想不透,但世界不管怎么变,文化的力量是不变的。我画阿伦特、加缪、康定斯基、维特根斯坦、齐泽克这些人的时候,我也不断翻看他们的著作和资料,我想知道他们对这个世界是什么态度,我也想知道这些人如何推动了世界,改变的能量来自哪里。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用以表达的语言到了无法再说的时候,思想就停止了,哲学到了研究语言哲学的时候,就已经到头了。实际上,艺术不止于语言,它提供了思考的场域。就像我想说的,藏在英国女王因为感冒缺席庆祝登基感恩仪式的那一天,画女王不是我的目的,我想记录一下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刚好那天女王身体不佳,缺席仪式,它实际变成了另外的想法的载体。
隐喻是一种态度
ARTDBL:八十年代以来,你的作品经历过多次转变,从带有政治批判意义和消费景观的表达,转向文化景观的内在的情境表达,今天转向了现实主义和隐喻。现实主义的观察方式,是否其实一直贯穿于其中?
杨国辛:今天和八九十年代的思考,确实有不同的地方。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片国土很贫穷,爆发的能量很小,从前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从电子时代、网络时代,一直到现在的 AI 时代,这个变化是我们看得到的,今天与世界融在一起了,经济体量也变大了,集中力量能办大事,但办不起错事!那个能量会更大。那么今天这片土地所发生的事情,对整个人类社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是否能成为我们所有人看待当下现实的角度?
1980年代,国门刚刚打开,思想很活跃,艺术家们的表达也很直接,到了九十年代后,实际上都在逐渐收缩,但即使这样,多少还有一些自由表达的空间。《参考消息》这件作品里,有很多政治、新闻媒体信息,我思考的是历史人物留下了什么痕迹和遗产,但我那时候相信,毕竟已经过去了,世界已经被打开,变得花花绿绿,一看,"巨人"已经不在了,但世界还要往前走,生活还在改变。
到了2000年左右,整个社会以经济为重心,消费主义盛行,时代一下子变得很光鲜,以前的苦日子,一下子变成高楼林立的世界,但我总是觉得太不真实,灯红酒绿里总带着一种脆弱感,到处充满了假象。我抱着怀疑的态度创作了《好果子》和随后的《江南》,想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多人都认为《好果子》很时尚,很好看,那属于误读,可能载体本身所呈现的力量和影响多少屏蔽了我的想法。那种非自然化的颜色像玻璃,又像塑料,很光鲜却是脆弱的,光斑也让人很迷糊。我为什么用“好果子”这三个字,那出自我老家嘴边的一句话,你以为你在追求美好,实际上“没你的好果子吃的!”但人们以为我真的在画“好果子”,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即使如此,我还是认可当时社会的变化。说白一点,虽然现代性对环境、生态、人们的价值观造成影响,但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无可厚非,相对于万马齐喑的沉默,那依然是一个好时代。
今年5月份,我去了一趟浙江天台山。作为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天台山隋代的国清寺被日本、韩国的天台宗尊为祖庭。我在里面一棵老梅树旁,还看到广东的老先生赖少其写了“隋梅”两个字的石碑,写得真好!但是寺庙里的东西在十年浩劫期间全毁掉了。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田中角荣访华的时候,他信仰天台宗的母亲托他一定要来祖庭拜访,周恩来亲自下令赶紧整修寺庙,从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地运来法器和文物。国清寺依山而建,建筑格局没有中轴线,唐代建筑的气势尚存,但我已经没有进去大殿内看看的兴趣了。
有时候想想,觉得很悲哀,我们今天要如何面对文化?最近一些艺术家在网络上受到了“审判”,过去几年都还在展出的作品,今天突然就被否认推翻。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ARTDBL:你不同时代的作品,都很敏感于时代的感觉,在今天的创作当中,你认为当下这个时代有何种把握?你认为当下正处于什么状态之中?
杨国辛:当下的环境里,后现代直接把现代缝合在了一起,科技手段让每一个人无处遁形,如果哪一天,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整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半硅基生命,而社会还赶不上科技发展的进程,到这一步,作为个体的生命体,自由是堪忧的。三年的疫情已经印证了这一点,不是上帝的眼睛盯着我,而是权力的眼睛在盯着我。
有天我和李邦耀老师开玩笑,当年林风眠把他的画放在浴缸里泡烂,然后从马桶里冲走了,我说小心有一天可能我们的画要被泡烂,从马桶里冲走,李老师调侃说你的画冲不掉,油画泡不烂,会堵塞马桶。这种对话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是不敢想象的,我们会把事情议论到这个点上,你可以想象已经发生了什么,才导致了语境的变化。发达的自媒体底下的网暴是前所未有的。今天这种文化状态,还能明白的说出什么?
ARTDBL:在你看来,隐喻在中国当下的艺术,是不是一种赖以生存的方式?
杨国辛:我所有的画面,都不止于画面本身,也不是手感的本能。我画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那时国际社会太冷漠,十年以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纪念这件事情时说,卢旺达事件使得联合国在主权与人权的关系中有了一个清醒的宗旨,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画英国首相约翰逊下台,转身的时候,国家依然平稳地运作,走了就走了,我很感慨。我画斯里兰卡的暴乱,人们冲进了总统豪华官邸,在游泳池里游泳,中国在这个南亚小国里投了不少钱,而对方像无底洞一样,不知道现在和我们还有没有关系,世界太复杂!
不能说隐喻就是这个时代的生存之道,但隐喻也是一种态度,即便是隐喻,也比既没态度,又没灵魂的"装饰"好。所以我的画的好像是隐喻,但态度还是明确的。
ARTDBL:你的图像来自于现实,现实中,图像可以被无成本且不限量地生产、复制、传播和消费,在今天,你如何看待艺术家对于信息图像再生产的意义?
杨国辛:这个时代的图像确实太多了,泛滥成灾,我曾经也想过重新画一遍的意义在哪,和现在的手机随手一拍有何区别。人的思考和意志会产生某种特殊性,当我面对信息和图片的汪洋大海,我的选择和语言转换,不是一晃而过的事情,将它们记录下来,组装归纳进了我的观念和思想逻辑当中,这就表明了我自己的态度和心境,至于能不能引起第三个人的共鸣,那是另外一回事。
抵抗虚无
ARTDBL:当你在画这些画的时候,你认为艺术是什么?
杨国辛:我这一辈子都在做艺术,但我从来没把艺术看作是很伟大的事情,也不敢说艺术家都必须站在制高点上讨论问题,我只是用所谓的艺术手段,记录下我的所思所想,仅此而已。艺术不过就是通往世界的通道之一,艺术可以是你的全部,但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艺术家首先要成为一个人,事实上,也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体,我也是个普通人在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绘画这种艺术创作是我所能够呈现的语言的话,应该是我作为个体的一种最真实的表达,我只有这个要求,这个时代说真话的已经不多了。
一位老学生和我聊天,问我今天为什么画得如此具象,我只想到“抵抗虚无”这个词。在当下这个震荡的时代,若无任何触动其实很难,如果还有人避开这个时代讨论“艺术”,还幻想着去追逐利益和名声,这对我而言,就是一种虚无,我做不到这样。
对历史的思考,对新知识的接受与每个人的追求有关系。我现在做的事情,谋的是“心”,有人谋的是“生”,我也不反对,肉体要运转,要燃烧,要吃,要喝。谋生就是谋生!创违心之作,谈违心之论,于我而言宁可游手好闲。我的画有意义就有意义,没意义也没意义,我也无所谓了。
ARTDBL:你从社会的、政治的、景观化的表达走向了个人的表达,从电子新媒介回归到一种可以信手拈来的日常化媒介,几乎回到了艺术家的个体、肉身和思考的本能动作上,当下这种状态也许是一种在限制状态下不得已的选择,但也对应了艺术史上很多艺术家在后期的创作中,都回归了本真。你认为如果不是出于疫情,出于自己的创作经历的话,最终会回到这个阶段吗?
杨国辛: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段,我不一定能够判断我的作品走向,但隐隐约约地,对这个时代还是有担忧,其实到了新世纪,我也在反思很多问题,但是疫情这个突发事件,对我来说冲击太大。2020年,我就在打边炉的文章里说,“一个时代正在退回暗影中,当下也许就是个分水岭”,就真的是一个分水岭。
封在武汉的时候,我看到人类的状况心里很是悲凉,唐宁街的狼、旧金山大街上的狐狸,巴塞罗那大街上的孔雀,全世界的人类活动都停了,成为了动物们的岁月。但是,到了上海被封城的时候,我的担忧就转向了我周边的人、所有的朋友,还有这片土地上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这种时候,让我如何还能安静地去思考纯粹的艺术,谈论艺术的本体?
ARTDBL:你会不会认为艺术应该超越时代,而不应该仅仅盯着眼下的苦难?
杨国辛: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太严酷,如果要脱离这个语境,去谈论别的什么问题,我觉得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闭着眼睛,什么都不说,讨论虚无和遥远,都不现实。博物馆里的古代艺术,那些彩陶上面,你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那些工匠们的劳作谈不到知识和文化层面,但他们在比现在更严苛的生存环境里所创造的图像记录,就反射了他们所接触的现实,现在回看,那种记录是很了不起的贡献。
前不久马蒂斯的作品正在北京展览,触动我画了一张“马蒂斯与模特”。马蒂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在那么混乱的年代,他的创作给人的心灵和视觉带去了安慰。他关注现实,也不离开对艺术本体问题的思考。但是,他看到人性深处最幽暗的一面,依然向往美好,他画的女模特都很可爱,很丰满,从几根线条里,你可以感觉到体香,这是他的伟大之处,这源自他对人性的理解,与他思考的独立性是分不开的。他面对教堂壁画的创作,并没有被动地在宗教场合的玻璃彩画上画耶稣像和圣徒像,他说要把灿烂和美带进去,你可以感觉到那种美好和能量,当中投射的就是艺术家的思考和个人的力量。我也曾在一幅绿色的窗外风景画里用了坂本龙一的一句话,他的表达和我有共鸣。武汉封城的时候他已经患癌多年,但他还为此做了线上音乐会,用音乐去抚慰困顿中的人们,龙一还能有这种心情,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我相信当人的意志力走向深刻的理解和表达,思想是可以在艺术上留下痕迹的,好的作品可以感染人,精神力量是强大的。
要用超越的态度去看历史
ARTDBL:图像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一览无余的,新闻图片也并非“透明的媒介”,拍摄、传播和观看,并不是中性问题,就像纳粹屠杀犹太人固然是惨剧,但当犹太人的资本去书写历史,历史依然是有选择性的。作为艺术家,你会像《参考消息》当中的毛泽东形象那样,在意当下所选择的图片背后的历史框架,以及追究图片的传播意图吗?
杨国辛:历史是动态的,历史的必然性总是藏在偶然性里,一个偶然和一个偶然,最后形成了必然。犹太人的历史就是犹太人的今天,为什么他们会发生这些遭遇?面对这些问题,所有的面对、关注、研究和思考都是正常的。保留广泛的声音,才是这个世界本来的面貌。自由讨论和分析历史,都没有错。不能说,画一条逻辑关系线,所有的人都要顺着这个逻辑去看待历史。
ARTDBL:如果不跟着某一条线索走的话,看待事物的眼光和个体立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杨国辛:看历史,我觉得还是要用超越的态度去看,就像今天的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历史上的纠葛和斗争不是孤立的。日本从“汉学”到“兰学”,到脱亚入欧的逻辑关系,与东亚文明和中国历史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明治维新,特别是黑船事件,美国强迫日本开门通商,日本的京都学派和上层的精英都认为他们的任务是解放亚洲,想用另外一种亚洲文明思想和逻辑关系去改变列强文明的欺压,但我们再跳一个层面来看,欧洲的工业革命已经改变了世界,潮流是不可抵挡的,这是京都学派思想破产的根本,他们局限于亚洲文明这个空间关系里,想用空间来替代时间,但时间已经走到了工业革命时代,他们没看清楚这一点。就像我们总是强调国情的特殊性,是否也把时间问题当成了空间问题呢?
人类很聪明,但也很盲目,很多行为都在不断地重复过去,这种历史太多了,总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不看世界已经走到哪一步。时间已经走向了今天这样一个文明形态,马斯克都已经向着火星去了。
就像这些绘画,一方面沉浸在现实语境当中,一方面又跳出来,现在所有的问题,我都想要跳出问题的层面往上一层去看。在贫穷的年代,我们大力搞阶级斗争,改革开放40年后,真正的阶层形成了,却不再提阶级了。十年动乱的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思考,现在回看历史,已经不能将它看为单纯的时间维度,我把它放在广阔的历史语境里去看,去问为什么。
ARTDBL:策展人称你为“隐者”,确实甚少在公开场合里看到你的身影,你如何看待这种隐者的状态?
杨国辛:人的认知是有障碍的,信息看似流通,人却越来越闭塞,众声喧哗时,你会感到更加孤独。在这个时代里,即使是家人也难以意见相合,找到能对话的人更不容易。
也是今年5月份,我到江苏常熟的虞山走走,那里有黄公望墓,有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老师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的坟墓,还有明末的钱谦益以及陈寅恪先生写过的柳如是的坟墓。这些历史人物都过去了,在历史的书写以外,现实中他们对待家园、对待文化是什么态度?有意思的是,柳如是的坟上还有鲜花,还有粉丝。明朝灭亡的时候,满清进关,柳如是对钱谦益说,国家没有了,我们去跳湖自尽。钱谦益在湖边摸了一下水说,夫人,水有点凉。柳如是看他不想死,自己跳下去了。钱谦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明朝东林党的领袖,屡次被贬后,南明建立政权,他又去投靠那些当年整他的人,从礼部侍郎变成了礼部尚书,清兵打进来后,他带着大臣开门迎接、投降、剃发,摸摸水,还不愿意死。很多人批评他没有气节、软骨头、没脊梁,不如柳如是。钱老先生这种才子,他对这些问题难道会没有意识?柳如是有气节,钱谦益真的没气节?
记得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说过一句话,是哪里人不重要,是不是人才重要。家园还在,文化还在,也许钱谦益比柳如是看得更远。但是,这样思考问题恐难以与人交流,很多场合,一些交流的内容也已经提不起我的兴趣,开口不慎容易把“天”聊死,不去也罢了。
今天不是谈地方性的时候
ARTDBL:你从武汉出生,来到了广州,武汉又成为了转折的发生地,请谈谈武汉和广州两个地方对你的影响?
杨国辛:我曾经也想过,或者我不离开武汉,也是可以的,那是我的故乡,我成长的地方。但现在,我反而不这样想了。最近因为父亲去世,母亲中风,我在武汉待了很长时间。有朋友问我,是不是还是觉得在故乡好?我想了想,故乡、他乡,此地、彼地,最终都是你要回归的大地。人在哪儿不重要,是哪儿人也不重要,是不是人才重要。
最近有朋友要写武汉美术界的历史,想要作一个采访,我婉拒了。我们这一生像坐过山车,跌宕起伏,但并没有走出这个循环,一地鸡毛的往事不堪回首,历史太复杂,永远不是单线的,我们所经历的只是历史的一个切片,所以,我很怕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雨果写《笑面人》、《悲惨世界》,这些大文豪对历史的判断不是简单的,现在回头去看法国大革命,是福还是祸,推动了世界还是分裂了世界,能说得清楚吗?这些文学家也有疑问,作品中只是展现其中的人性。说白了,所有的战争、瘟疫、灾难都是人性的冲突,无论身在何处,总要面对人的复杂性。
电影《英国病人》里有一句我认为很重要的台词:希望这个大地没有地图。作者迈克尔·翁达杰是加拿大人,他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模糊了人物的地域身份,将不同族群、不同阶层发生的战争,破坏与信仰,爱、忠诚与恨结合在一起。一个没有地图的世界是不分族群和国界的,实际上,这很难实现,就像《圣经》里的巴别塔,如果没有语言的边界和政治,人类可能已经成为了神。人类这个物种很聪明,正因为如此,事情好做,人难搞,也因如此,人类发展过程中,障碍的力量大于进步的力量。
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很多艺术家走向了在地性研究,从大的层面上讲,今天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谈论局部问题的重要意义在哪?就像唐德刚写的《晚清七十年》,当时中华大地发生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解决什么?可能在某个时段里谈地方性是有意义的,但不是今天。
ARTDBL:你如何看待自己当下的创作状态?
杨国辛:当下,艺术并不是我最重要去做的事,重要的是照顾好中风的母亲,让她很安稳很平静地走过最后的时光。偶尔画一画,都只是占据时间和空间的副产品,面对人生的时候,艺术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
再远的事情无法驾驭,也无法预测,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做好我自己,钱理群说这是一个“三无时代”,无真相,无共识,无确定性。老先生说得太准。据说他们老两口住在养老院里,患有癌症也拒绝治疗,这些人对生命的思考已经想得很透了,晚年的路,就是由疾病伴随的。我的父亲在今年的第二波疫情中感染了新冠病毒,不断低烧,熬到6月20日去世了。去世前,在医院里,主治医生建议进ICU,我拒绝了,我不建议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还使用一切具有创伤性的,使人很难受的治疗手段,最后我签了一份协议,希望父亲可以平静一点走完最后的路,我一直守着他,直到心电图最后变成一条线,给他擦擦澡,换上衣服,送走了。我想起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要能躲过这场灾难兴许还能活几年。但他最终没有躲过。这种动荡的岁月中,你还能醉心于谈什么艺术?
-
阅读原文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数艺网立场转载须知
- 本文内容由数艺网收录采集自微信公众号打边炉ARTDBL ,并经数艺网进行了排版优化。转载此文章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标注“作者”、“来源:数艺网” 并附上本页链接: 如您不希望被数艺网所收录,感觉到侵犯到了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数艺网,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及时处理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