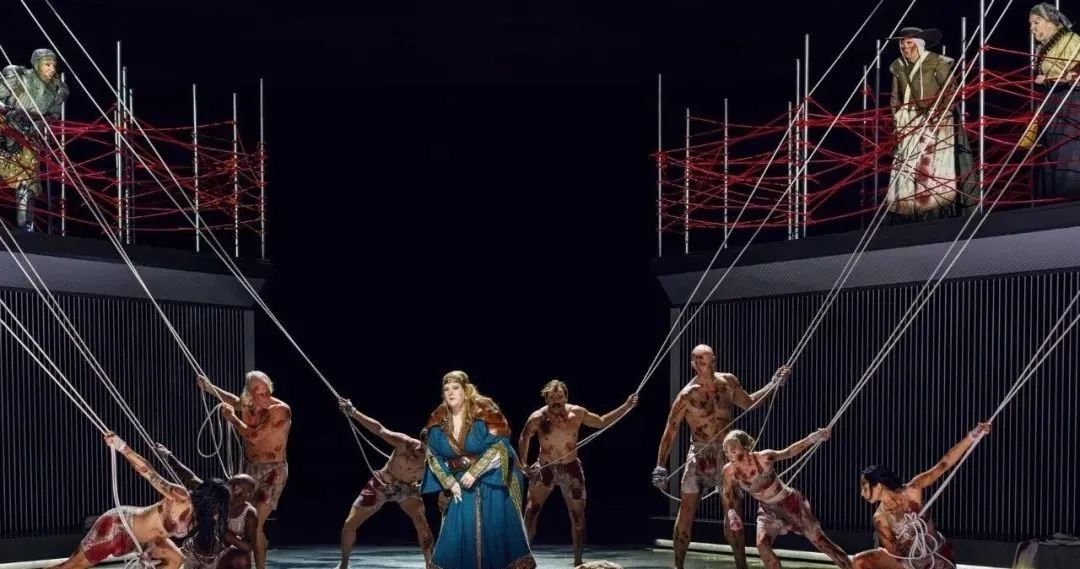- 0
- 0
- 0
分享
- 观演行动矫形术:沉浸式剧场观演权利差异化现象研究
-
2022-11-11
本文转自:戏剧艺术
内容摘要:在沉浸式剧场“观演行动矫形术”的操控下,沉浸式戏剧创作者赋予观众的差异化观演权利与观众观演行动本体论意义上的“否定性”形成既相互对峙又彼此依附的辩证关系。沉浸式剧场观众在接受差异化观演权利机制的同时,也在应允相应的权利让渡,在否定创作者设立的选择边界时,也在改写创作者植入的干预边界。沉浸式剧场“观演行动矫形术”始终处于不断自我调试的弹性生长空间。沉浸式剧场观众差异化观演行动背后的主体建构力既是沉浸式剧场价值的独特生产方式,亦是其生产价值本身。
关键词:沉浸式剧场 演出技术工程 观演权利差异化 观演行动矫形术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22)05-0010-12

王嘉嘉
大理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影视学博士,师从中国著名戏剧导演王延松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近年来主要围绕中国当代导表演美学与东西方沉浸式戏剧开展创作与研究,曾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戏剧学科建设丛书”之《“古陶俑”<原野>的世界表情:英文版<原野>创作排演纪实》,于《戏剧文学》等学术刊物发表《古陶俑<原野>的世界表情——关于“古陶俑”<原野>的创作对谈》《王延松带我走进沉郁“原野”》《“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东方扮演”<奥赛罗>的台前幕后》《沉浸式戏剧观演关系研究》《沉浸式戏剧的“非线性叙事”与多重“审美快感”》等文章。
导语
沉浸式戏剧自问世起便以其观众获得的非比寻常甚至无限可能的观演权利而备受关注。沉浸式戏剧观众与演员、空间、道具等诸多元素的近距离互动固然打破了传统剧场远距离观演关系中的主客、动静等二元对立状态,产生转客为主、转静为动的显性变化,呈现出灵活多样的观演交互性,然而即便如此,沉浸式剧场观众却未曾获得亦不可能获得完全的观演自由与绝对的观演权利。反之,正是通过一系列我们视而见之及我们视而未见、见而未察的演出技术工程,沉浸式戏剧创作者们缔造出非凡的“观演行动矫形术”——对观众而言既充满权利诱惑又布满权利限制的差异化观演权利体系、机制与价值。
一、观演权利差异化的体系建构
沉浸式戏剧创作是由诸多创作部门组成的复杂创作系统,这其中包括故事设计、空间设计、时间设计、表演设计、舞美道具设计、音乐设计,以及灯光、特效等各部门的设计创作。如此来看,沉浸式戏剧创作所涉部门似乎与传统舞台戏剧大同小异。然而,上述创作分工中遗漏了一项对于沉浸式戏剧创作而言极为重要甚至统领以上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沉浸式剧场观众的观演权利差异化体系设计。
在沉浸式戏剧创作中,观众群体定位(年龄、性别、职业、身份、爱好、审美等)、观众的总量、观众进场的分流数量、观众观演路线的数量、各路线上观众的分流数量、观众观演的互动频次,以及观众行动和选择的自由度定位(如可否自主选择佩戴观演面具、可否自主选择走哪条故事路线、可否自主选择扮演剧中哪个角色、可否自主选择改变故事走向等)都将直接或间接决定沉浸式剧场创作的各个环节和剧场演出效果,因为“加入作品中的每个自由意志元素都将大幅度增加各个技术工程部门的设计任务”。[1]因此,沉浸式戏剧创作首先需要着眼于观众观演行动和观演自由的设定。
“行动”(act)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中的“archein”与“prattein”两词,前者意指“引领”和“统治”,后者意指“经过”和“完成”。[2]即“行动”就其原初语义而言,并非单方面的“统治”或“完成”,而是双向并行的两位一体,且必然伴有“权利之差”。对此,柏拉图曾在著作《政治家》中直言不讳地指出:
真正国王的技艺不是为了它自身而运作,而是为了控制那些指导我们行为方式的技艺。[3]
政治家会让所有其他人接受训练——这些人事实上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像国王那样织造城邦,但愿意成为材料,让国王能够科学地把他们织成一个整体。[4]
柏拉图所论及的建造城邦的政治家与作为建造城邦材料的其他人的内在关系同沉浸式戏剧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隐秘关系极为相似。这种“事实上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像国王那样织造城邦,但愿意成为材料,让国王能够科学地把他们织成一个整体”的民众所接受的“训练”正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曾指出的“社会矫形术”(orthopédie sociale)——即通过权利经济学所言及的控制机制、监视机制与生命政治学所论及的体验机制对民众“可能做、能够做、趋向做”的行动行使监视、预防、引导、纠正的行动矫形术。[5]这一机制原理深度暗合了沉浸式戏剧创作者透过剧场演出技术工程向观众发出允许、禁止、鼓励、阻碍等隐形指令以训练和操控其观演行动模式的“观演行动矫形术”。为深入阐析这一机制原理,我们首先需要阐明沉浸式剧场观众观演自由的范畴和观演权利的边界。
关于何为自由,“形而上学传统一直将自治(sovereignty)看作是理想的自由,即自由就是自治,绝对的独立自主,完全的自足与控制”。[6]对此,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曾批判地指出理想自由存在的不可能性及将其等同于完全自治的荒谬性——因为“自由需要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的实在性又是遭遇另一个不同的自我意识,即遭遇他者并被他者‘承认’时才产生出来”。[7]可见自由无法达到理想中的完全状态,因承受他者的限制和羁绊只能在某一限定范围内来回震荡。
关于何为沉浸式戏剧观众的观演自由,沉浸式戏剧创作者杰森·沃伦(Jason Warren)[8]在其著作《创造性世界:如何创作沉浸式戏剧》(Creating Worlds: How to Make Immersive Theatre)中将其定义为,“创作者在沉浸式戏剧创作过程中赋予观众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观众行动的自由和观众影响故事的自由”。[9]
根据观演过程中观众所获观演权利的差异,杰森·沃伦进一步将沉浸式戏剧划分为探索类、引导类、互动类。[10]各类作品特点及观众权限差异如下表所示:[11]

从上述三种沉浸式戏剧的对比来看,沉浸式戏剧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先继承传统镜框式舞台剧创作方法然后又一步步脱离其既定规则的探索过程。沉浸式戏剧观众的观演权利依托以下各项指标:
1.观众是否可以在剧场自由行走并自主选择其观演路线;
2.观众是否需要佩戴面具将自己的内心活动与情绪反应等个体特征隐匿起来;
3.演出是否具有一对一的专属于个人的观演体验机会;
4.演出是否设有多次互动机会,是否能为观众提供高频参与式体验机会;
5.演出是否依据观众的行动和选择而改变故事结构与故事结局。
正是在上述诸多“是”与“否”的选项中,不断形成选择的量变,生成类型的质变,从而演化成沉浸式剧场独有的观演权利差异化体系。
无论是哪一类沉浸式剧场,创作者赋予观众的观演权利都不可避免地会有所限制。这些限制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构成不同类型沉浸式演出中观众的权限边界,因此沉浸式剧场观众所获得的观演自由并非完全的自由,沉浸式剧场观众总会做出不同程度的权利让渡。为确保观众的自由度保持在创作者相对可控的范围内,创作者曾根据创作实践总结出观众自由需具备的两种特性,并进一步提出沉浸式剧场演出“技术工程”的总体概念:
1.对观众而言,自由必须在各个层面具有意义。如观众的自由应对作品造成一定的冲击力。
2.对演员和制作团队而言,观众的自由应该在可管理范围内。
我们需要一套稳固的、事先规定好的方法,在观众对作品产生贡献时,能够将其贡献消化并融入作品当中。这些方法就是我们的技术工程。[12]
可见,在沉浸式戏剧创作者眼中,观众的观演自由应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可预判、可规划、可转化、可操控的管理范围内。然而,观众的主体意识(超越性)和行动本性(否定性)告诉我们,观众不可能对于沉浸式剧场观演权利差异化体系的“游戏规则”全盘接收,这势必引发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权利较量”。为此,沉浸式戏剧创作者设计出一套不断自我调试、更新的差异化观演权利运行机制,以调节观演关系的平衡,保持观演关系的张力。
二、观演权利差异化的运行机制
沉浸式戏剧观众观演权利差异化的体系建构并非单纯的理论建构,而是始于实践、反哺实践的理论提纯,是创作者在创作实践中由宏观到微观、从显性到隐性不断总结归纳出的创作规律。这些规律隐藏在沉浸式戏剧演出的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的运行机制中。
首先,在叙事时间的规划上,观众从入场开始就因入场先后顺序的不同而被分流,从而被引入不同的故事线节点,通往不同的故事轴线,获得不同的观演权限和观演体验。当观众正式进入演区后,其一举一动仍将被隐形的技术工程所引导。如观众将被创作者为其设计好的“强制选择”(Forced Choice)与“暗示选择”(Implied Choice)左右自身选择。所谓“强制选择”指创作者公开并明确提供给观众的路线选项。[13]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观众拒绝“强制选择”后做出的选择,也常是创作者提前设计好的选项之一。而所谓“暗示选择”则指表面上由观众自己做出的选择,实则为观众根据剧场内各种感官暗示做出的选择。这些选择不必涉及路线方向,可以仅仅是关于剧中信息传递的选择,如观众选择是否将自己所知道的实情全部或部分告知剧中角色。[14]可见,在沉浸式剧场中,无论是面对“强制选择”还是“暗示选择”,观众的自主选择权都常处于让渡状态,或自愿让渡或非自愿让渡,或有意识让渡或无意识让渡。个中原因有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论》中所论述的那样:“只要一个人占有任何土地或享用任何政府领地的任何部分,他就因此表示他默认的同意,从而在他同属于那个政府的任何人一样享有的期间,他必须服从那个政府的法律。”[15]沉浸式戏剧观众从踏入沉浸式剧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接受来自沉浸式戏剧创作者这一“特殊领地管辖者”立下的匿名“契约”,他们在剧场中行走驻足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履行默认的“同意”,服从默认的“法律”。这种服从机制秘而不宣,其运行方式极为隐蔽,运作工序极为复杂。无数个“强制选择”与“暗示选择”巧妙分布在故事运行的特定时间节点与时间轴线上,这些点与线包括故事的“汇合点”(Junctions)、故事的“路线”(Paths)与故事的“线程”(Threads)。所谓“汇合点”指故事走向可以被改变的时刻,即各条故事路线行进的交叉路口,观众在此做出的选择将引其步入不同故事路线。[16]而“路线”指往返于故事各“汇合点”之间的故事片段,即由观众选择构成的个性化、差异化故事片段,观众在此拥有行动自由,但其自由选择不会改变该片段内的叙事走向。[17]所谓“线程”则指故事在受到观众选择影响下生成的分支。[1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如“路线会互相排斥,因为它们同步发生”[19],因而没有哪位观众能一次性完成所有路线的体验,即没有哪位观众能一次性看到演出全貌。同时,“每位观众选择的路线都将会决定该场演出中所遵循的线程。一旦演出完成几个场景后,其潜在的线程数量就会变得庞大”[20],观众和演员由此共同编织出一张变化万千的相互制约、彼此拉扯的行动关系网。最为精妙的是这些技术工具在运行时产生的障眼法,即“观众不会觉察到汇合点与路线之间的差别。他们并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会影响叙事……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被给予选择的能力,他们感觉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同等重要”[21],而当观众由于过度兴奋或专情于某一场景从而使该场景的互动环节严重超载时(如由原计划的5分钟超时至10分钟),为避免叙事脱轨或全剧瘫痪,创作者会在创作中提前预判和埋设多个“同步点”(Sync Points),以将剧中不同路径、线程的错位拉回正轨,使其重新归至同步节拍。[22]最终,当观众完成一系列或明或暗的选择并生成各自不同的选择组合后,他们也便完成了各自独特的沉浸式戏剧之旅。
除却时间规划上左右观众选择的隐形机制,从空间设计的最细微处查看,还可以发现创作者埋设了多种藏踪蹑迹的“干预边界”[23],如创作者在某一个场景空间内或两个场景空间的连接处通过观演互动、实体物件、灯光暗影等元素制造出的影响观众选择的“行动边界(Action Boundary,由行动制造的边界)、“物质边界”(Physical Boundary,用物件制造的边界)、“灯光边界”(Light Boundary,用光影制造的边界)[24]。凭借这些由视觉、听觉、触觉乃至嗅觉、味觉构成的“知觉边界”,创作者在各场景空间内及各空间连接处创造出引导观众聚散、进退的“拉力”(Pull)与“推力”(Push)。所谓“拉力”指使观众进入某空间区域的力量。反之,“推力”则指使观众离开某空间区域的力量。[25]创作者通过构建多种“拉力”与“推力”组合,完成对观众群体的分流,以阻止观众在观演过程中随意聚散,即达成适时且有效的“分开观众”(Dividing the Audience)的目的。[26]具体操作方式包括:
1.分裂观众(Splitting the Audience),意指通过两个同等“拉力”把一群观众分成人数大致相同的两个小群体,使其流向两个不同的空间。[27]
2.分切观众(Shaving the Audience),意指通过两个或更多的“拉力”且其中一个拉力明显比另一个高,来鼓励一小群更有冒险精神的观众去往更远处的空间探索。[28]
3.分散观众(Dispersing the Audience),意指通过一系列小事件形成“推力”,使观众从某一空间的多个出口离开此地,去往多个方向。[29]
由此可见,沉浸式戏剧创作者通过精心设计的技术工程对观众观演行动实施的矫形术无处不在,对观演权利的限制无孔不入。因此,我们所谈及的沉浸式戏剧观演体验的多样化、个性化并非是基于观众观演行动的绝对自由化,而是基于观演权利的差异化。
然而,无论上述观众观演权利差异化体系的建构如何坚实牢固,观众永远会在沉浸式剧场为创作者带来惊喜。这份惊喜来自观众对“观演行动矫形术”的否定与反抗。一个较为鲜明的案例是观众在沉浸式剧场里拒绝佩戴观演面具。研究者约瑟芬·马雄(Josephine Machon)曾在其著作《沉浸式戏剧:当代表演的亲密性与即时性》(Immersive Theatres: Intimacy and Immediacy in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中如是描述此现象:“我曾亲眼目睹一位观众在观看潘奇醉客剧团(Punchdrunk)的作品《浮士德》(Faust)时拒绝佩戴面具。她用这一行动拒绝作品的演出形式并提出‘我知道我的浮士德’,暗示此类古典作品该用怎样的既定表演方式来表演。”[30]此类现象不胜枚举,如创作者杰森·沃伦曾坦言:“我们已经引导观众到我们想要他们去的地方,但我们没有消除或明显地阻止他们做出相反选择的能力。无疑,偶尔会有个爱冒险的家伙极力抗拒我们设置的地带和流向,折向相反的方向。不要假定你能控制你的观众,我们所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影响他们。”[31]
如果说沉浸式剧场观演权利差异化机制是充满“奖惩机制”的观演行动矫形术——“在鼓励观众遵循故事走向和惩罚观众按自己的方式探索作品世界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限”[32]——那么上述沉浸式剧场里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情形则提醒我们不可小视甚或无视观众主体意识的存在,不可轻易划出和划错这条微妙的界限。这是因为,“当你把你的观众驯化得非常顺从时,你再想改变其行为将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如果你真想让你的观众在任何时候都能主动行动,你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才能实现。每当你奖励一个观众跟随群体,你就会使不跟随群体的选择变为一个越来越无趣的选择。这不仅会影响观众怎样行动和向哪儿行动,还会影响他们如何与演员互动”。[33]如果说沉浸式戏剧创作者因惧怕观众发出的挑战而过度依赖“观演行动矫形术”,从而对观众的自由强加遏制甚至扼杀,那么他们所创造的技术工程也就不战而败了;如果说沉浸式戏剧创作者因惧怕伤害观众的自由而任由观众自主行动,那么他们所创造的这种为保障沉浸式剧场演出顺利运行而干预观众观演自由的“观演行动矫形术”也就失去了斗志。
幸好相反,沉浸式戏剧创作者不仅期待观众以配合的方式参与到沉浸式剧场的新型观演模式与叙事模式中,而且他们也期待观众以富有创造力的否定性行动来参与叙事、推动叙事。如在“互动类”沉浸式戏剧中,观众的选择不仅可以改变叙事弧线的走向,而且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故事结局。即便是在观众行动无法改变叙事走向的“探索类”与“引导类”沉浸式剧场中,为吸纳和转化观众否定性行动带来的冲击力,创作者们也会在排练伊始就将排练内容划分为“固定链条”(Concrete Strand,已编好的固定情节、人物动作、台词等)与“互动链条”(Interactive Strand,演员与观众的互动、观众与空间的互动等)[34],并在两股链条的合成排练中安排“压力测试”(Stress Test),即通过一种“假设排练”(“What If” Runs)来排查技术工程中存有的缺陷,来测试技术工程的极限。[35]比如在“假设排练”中,创作者常会向演员抛出意想不到的“互动”(由各部门创作人员或某些演员来扮演观众,给出意料之外的互动行为),以此磨炼演员面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36]同时,为进一步确保演出无论遇到怎样的观演行动都不会出现失控,创作者们还会在“互动链条”的排练中安插几位“浮动演员”(Floating Cast)——这些演员只负责参与演出中的互动环节和即兴环节,他们具有更高的应变能力和修正能力,不仅能在演出中及时侦查和补救叙事脱轨现象,还能为了展现出更好的演出效果而以角色的名义开启剧本中未曾铺设的故事情境,以激发观众兴趣、扩展观演体验。[37]
可见,对沉浸式戏剧创作者而言,剧场中所有出乎意料的、具有挑战性及反抗性的观演行动不仅不应被视为令人惧怕的造成叙事坍塌的炸弹,反而应被创作者预判和化解为可助其发现剧场技术工程漏洞、寻找问题解决方案、提升技术工程效力的机遇。换言之,沉浸式剧场演出若想取得成功,不仅需要观众做出一定的权利让渡,也需要创作者做出一定的权利让渡,即达成创作者的“干预边界”与观众“选择边界”的相互调试。例如,潘奇醉客剧团在其后续创作实践中巧妙地吸纳了演出中曾有观众提出的摘下观演面具的不情之请,主动设计并推出一系列特定场景,不仅允许观众摘下面具,而且还允许其关起门来与演员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更为私密的观演互动。[38]这种摘下面具的观演特许和一对一的观演特权可谓沉浸式戏剧观演权利差异化机制的明证。
三、观演权利差异化的生产价值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德]马克思、[39]沉浸式剧场观演权利差异化机制不仅创造了新型的差异化观演关系、差异化观演行动与差异化观演体验,而且还创造了新型的剧场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与生产价值。
对此现象,研究者亚当·奥尔斯顿(Adam Alston)在其著作《沉浸式戏剧之外:美学、政治学与生产性参与》(Beyond Immersive Theatre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Productive Participation)中曾指出:“表演者和生产性参与者的情感劳动作为一种生产方式,颠覆了非物质性生产的价值——这种价值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框架中被利用并转化为资本。”[40]沉浸式戏剧观众因其在沉浸式戏剧观演过程中所付出的“身体”和“情感”的双重劳动而成为“新自由主义生产者”。关于这种新型生产者的群体特征,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生命政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中指出,这是一群具有企业家特质的主体,其自身能力构成了资本生产来源的基础。[41]关于这种新自由主义生产者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式,哈尔特(M. Hardt)曾将其总结归纳为“身体劳动”(即以身体参与为媒介的信息交流)和“情感劳动”(即以情感展示为质料的面对面服务)。[42]在沉浸式剧场中,演员表演时会吸引观众近距离围观,演员能在咫尺间感受到观众的慌张喘息、交头接耳、手足无措或试探性触摸,从而激发其表演,而观众也会“直接感受到演员的汗水和体力消耗;直接感觉到演员的痛苦以及演员声音的要求”[43],从而激发出其自身的情感反应与身体反应。除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共同劳作,观众与观众之间也存有相互间的情感共振、身体共鸣。
笔者认为,在沉浸式剧场的整个观演过程中,除却上述观众和演员的“身体劳动”和“情感劳动”两种显性的生产方式外,观众和演员还在以其隐秘的意识活动付出着持续的“意识劳动”,且即便是显在的“身体劳动”与“情感劳动”全部停摆或缺席,潜在的“意识劳动”仍在无声运作。或言,恰恰是内在的意识活动滋生并建构着外在的情感活动与身体活动,因为现象学家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Robert Sokolowski)曾指出:“意识的内在之流被安顿于发生在世界之中的过程里面,但是它也面对着世界,为世界得以显现而提供诸多意向活动的结构。”[44]对沉浸式戏剧观众而言,其观演权利差异化生成的观演路线差异化、事件序列差异化、场景序列差异化,以及每个时间节点与时间轴线上的意识、情感、身体浸入的“当下”的差异化势必使其获得不同的外在时间体验,而不同的“当下”因连接着每位观众不同的过去与未来,势必促使其产生不同的“内在时间意识”。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直接经验中,我们不只是拥有被给予我们的当下的画面;在我们最基本的经验中,我们还拥有直接被给予的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感觉”。[45]即便是两位年龄相仿、背景相似的观众并肩走入同一观演路线,同时经历完全相同的场景空间,其内在时间意识仍会有所不同——因为在走入沉浸式剧场的前一刻他们经历了过去的不同,在走出沉浸式剧场的那一刻他们将步入未来的不同,在游历沉浸式剧场的每个同一刻他们被唤醒的当下和“直接被给予的关于过去与未来的感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言及的“不同”不仅包括两位观众所获体验的不同,还包括每位观众自身产生的变化。这种由剧场外的个体经历不同和剧场内的体验不同共同造就的差异化“意识劳动”正是沉浸式剧场所呼唤的差异化“身体劳动”与“情感劳动”的沃土和源泉,这是因为,“内在时间意识不但构造我们的意识生活的内在时间性,也构造世间事件的客观时间性。对于所有其他形式的意向性构造具有的时间性来说,内在时间意识都是核心”。[46]
可见,沉浸式剧场价值生产所依赖的劳动时间不仅包括创作者和演员在剧场演出之前及演出当中所消耗的劳动时间,还包括观众在沉浸式剧场演出中所付出的“身体劳动时间”“情感劳动时间”与“意识劳动时间”,甚至还包括观众在走入剧场之前和走出剧场之后因期盼、设想、回味等意识活动而消耗的“意识劳动时间”。而由于沉浸式戏剧表演过程中常存有较高频次的即兴互动,演员时常会受到来自现场观众身体的、情感的、意识的反触动,激活其自身过往的人生体验、表演经验及内在时间意识,从而创造出鲜活的、只属于这一刻的、不可复制的互动体验,因此,演员的内在时间意识作为极为宝贵的“意识劳动”生产质料,也被投入到沉浸式剧场的价值生产中。
关于沉浸式剧场的独特价值生产方式,除了观众的“身体劳动”“情感劳动”与“意识劳动”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观演行动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否定性”也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现象学研究者曾提出,“本体论中的否定性,在形而上学之中被认为是时间,而在现象学中就是人类的行动”。[47]这是因为,“行动是否定性在现实中的运作:人存在于时间之中,行动既会改变(否定[negates])既定的现实(存在[Being]),也会改变行动者(生成[Becoming]),因为行动者通过被转变的现实反思自身,再通过行动超越自身”。[48]对此,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也曾总结道:“人的本质就是行动,而行动的本质就是否定性(Negativity)。”[49]人类不断地通过行动生产、赋予、分配权利,又不断地通过行动否定和反抗权利,两者之间交织着永不止息的原生辩证关系,这是因为,“哪里有生命遭遇管理和控制程序,以及开发和榨取程序,哪里的生命就会相反肯定自己的创造威力……哪里有权利行使于生命,哪里就有生命进行创新。哪里有权利迫使生命屈服,哪里就有生命实施一种本体论的,也是政治的战略,以此进行反抗:一种创造就是一种存在的增强”。[50]可见行动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否定性,并非指向粗暴的破坏性,反而指向人类永恒的创造性与超越性,是人类更为本质、更为强劲的生命存在方式、权利生产方式与价值生产方式。
在沉浸式剧场中,无论是观众还是演员,都既是行动的施动者,也是行动的受动者。在不断更新、裂变的行动之网中,没有哪个人能够完全按照其既定行动计划行事。即使是在观众不能改变故事走向的“探索类”沉浸式剧场中,观众在差异化观演权利机制下所做出的一系列“否定性”行动(如违背佩戴观演面具的要求而摘下面具,如违背不许挪动或拿走剧场内物品的要求而偷偷打开一扇紧闭的窗,或拿走一件藏于抽屉的物件),这些行动都将改变观众的个体观演体验,并将改变其身边演员的表演方式与其他观众的观演体验,因为“最微小的行动,在最受限制的环境里,仍然携带着无边界性的种子”。[51]
可见,沉浸式戏剧观演行动的否定性总会潜移默化地重塑观演机制,从而重塑他者,重塑自身。观演行动的否定性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可以清晰地看见行动间的相互关联并追根溯源)与“蝴蝶效应”(难以直接查见行动间的相互关联和追溯缘由),在沉浸式剧场不断发酵,势不可挡。这是因为,人类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磨灭的主体建构力,“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构建自己,因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变其自身的主体性,从来没有停止在无限众多的系列主体性中构建自己,这些主体性永远不会消失”。[52]人类的“主体性”永远处于“运动”之中,其不断建构自身又不断摆脱自身而产生的“超越性”正是人类不断创造自我、突破界限、书写历史的必然产物。[53]沉浸式剧场差异化观演行动背后的主体建构力正是创作者惊喜发现并努力运用的沉浸式剧场特有的价值生产方式与价值本身。
结语
综上所述,对沉浸式戏剧创作者而言,无论是通过巧思善工向观众撒开行动之网,还是通过差异化观演权利向观众递交权利之杖,都无法达成也不应达成完全的观演自由与完全的观演束缚。这是因为,“任何系统接近了完美操作性,也就接近了自身的死亡……追求总体完美就是追求总体背叛,追求绝对可靠就是追求无法挽回的衰退”。[54]拥抱观演行动“否定性”带来的创造与惊喜,吸纳观演行动“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与快感,这才是沉浸式戏剧创作的生存之道。
对沉浸式戏剧观众而言,沉浸式剧场观演权利差异化机制向其敞开了一个邀请其身体、情感、意识集体参与创作的场域。这个场域既蕴含了给予,也包含了获取;它既激发了打破,也孕育了创造;它既滋生了抵御,也滋养了共享——给予差异化观演权利造就的差异化观演体验,获取差异化观演权利促生的差异化观演行动。它打破原有单一化物理距离形成的观演界限,创造新型多样化知觉性观演边界;它抵御绝对观演自由引发的叙事崩塌,共享相对观演自由带来的剧场价值。
所有创作过程与观演过程中的两极运动都向我们发出共同的警示:沉浸式戏剧欲蓬勃发展,离不开创作者对新型观演关系的维护、对新型观演行动的呵护,因为“在行动之外并不存在一个更高的目的”。[55]切勿用“观演行动矫形术”伤害观众的创造性,切勿迫使其观演行动沦为目的论与工具论中失却本体价值的、用而弃之的手段。
作者单位:大理大学艺术学院
本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仅做分享使用,不做商业用途,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如果分享内容在版权上存在争议,请留言联系,我们会尽快处理。
-
阅读原文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数艺网立场转载须知
- 本文内容由数艺网收录采集自微信公众号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并经数艺网进行了排版优化。转载此文章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标注“作者”、“来源:数艺网” 并附上本页链接: 如您不希望被数艺网所收录,感觉到侵犯到了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数艺网,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及时处理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