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 0
- 0
分享
- 与陈小文、李振华、毕昕对谈 媒介与技术的可介入性:中国数字艺术策展三十年
-
2025-08-27
本文来自于 https://www.on-curating.org 网站,经过数艺网编辑后发布,并附上原文链接:https://www.on-curating.org/issue-56-reader/媒介与技术的可介入性中国数字艺术策展三十年.html
受访:陈小文、李振华、毕昕
采访:李汭璇
李汭璇(以下简称“汭”):三位各自是如何进入数字艺术策展领域的?来自不同时代的策展人,所要面对和处理的环境、语境、主题、形式都有哪些差异?
陈小文(以下简称“陈”):我最初接触数字媒体艺术是在1996至1998年期间。1996年我去阿尔弗雷德大学工作,与同事教员一起从事数字媒体艺术创作和教育。这些同事早期都在做电子艺术,他们创作的媒介是模拟信号,直到96年他们才开始用电脑进行创作。
在90年代的美国,数字媒体艺术算较新的专业。央美的领导和外办主任朱竹提出是否能把数字媒体教学带到央美,于是2001年,我在央美办了中国数字媒体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个讲习班,这是一次中外联动的国际活动。随后,央美开始组建数字媒体艺术教育专业方向(2003年正式通过教育部批准)。讲习班开班一周后,张培力就过来和大家交流取经了,当时他正在中国美术学院主持组建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所以可以说央美和国美几乎是同时建立起了这一专业方向。
2001年,国美的邱志杰老师还有几个教员、学生组织了《附体》展览。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中国较早期的数字艺术展览之一。这个展览显然不是官方的,也没有策展人,就是年轻艺术家在一起做事,展览费用也是大家凑出来的。这特别符合中国早期的策展方式,艺术家兼具了策展人的身份,大家共同努力。现在这种形式少了,其实我觉得应该变得更多样化的。我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多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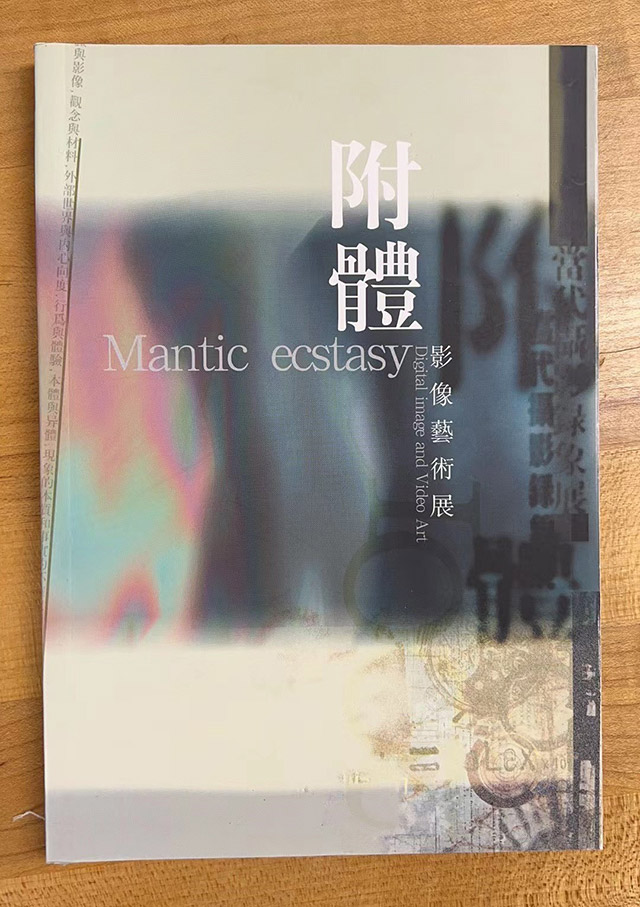
2002年,我组织了一个数字及传统媒体艺术交叉领域的研讨会,宋东、高名潞、费大为和张培力都应邀参加了。从费大为那我得知,巴黎的中国艺术家在做交互影像,对此我很兴奋,因为当时我也在尝试做我的第一个交互影像作品。随后的几年我来到央美教授交互影像的课程。简而言之,我的经验涉及到了中美经历的交叉及互相之间的影响。
李振华(以下简称“李”):我从1999年开始专注做媒体艺术,当时我在英国的IC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1 接触了很多以数字为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和项目。之前我也常与邱志杰、吴美纯,及很多艺术家一起工作,做了许多好玩的展览,其中也包含了“后感性”(Post-Sense Sensibilities)系列展览线索下的一些实践。这些经历激发了我的兴趣,不仅涉及新媒体和数字艺术,还触及更宽泛的实践。
刚才陈老师梳理了新媒体艺术教学的线索,我想再补充一条实验艺术教学的线索。
零几年时(2000年后),我们就在讨论什么是“实验艺术”了——是“试验”还是“实验”?所以说,实验艺术和新媒体艺术一样,都是从90年代末众多人的工作中显现的。那时艺术家刘韡就在用非常基础的电脑创作绘画小稿,最近听崔灿灿讲起90后艺术家在创作中使用“电脑图像美学”时,我就联想到,很早之前就有艺术家在做这样的事了。
此外,在英国的线索里,2000年至2004年间提出的概念——Live Art(现场艺术)2也是我和邱志杰在九九年的工作中重点讨论、关注的元素之一。其实我们并未把这些艺术形式局限于新媒体艺术,因为这些实践可能包含了1999年以来,所有重要实验艺术转向的开端。
数字艺术之前,就是录像艺术。到了2000年左右,我们开始有了所谓关于Digital Art 的讨论。从那时起,我、邱志杰和吴美纯开始做“藏酷新媒体艺术节”。这其实是个很小的项目,在我看来有趣的是里面应用了当时特别流行的一些新媒体艺术形式,比如说CD-Rom Art (光驱艺术),就是把光盘放电脑里,通过选择菜单的方式交互,现在回想起这些觉得太逗了。
谈到交互艺术,我特别推崇邱志杰做的《西方》(1999年),因为他用了一个特别简略的,PowerPoint的软件来做交互。其中植入了声音和影像,同时又涉及大量有关东、西方的概念。至今我都认为这是新媒体领域里的一件超级大作。
1994年,冯梦波就开始使用苹果电脑了,3, 4 当时大多数人还在用PC。此外,胡介鸣老师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讨论交互和监视的问题了。5 他当时就有一个非常简约调控器,通过监视器来看普通人和楼道等等。我觉得,那时大家一方面开始有了媒介使用上的意识,另一方面有了媒介批判的意识。
1997年,冯梦波和汪建伟参加了卡塞尔文献展,这都是中国新媒体艺术领域的里程碑。再说到国际大展, 2002年由澳大利亚策展人Kim Machan 在世纪坛做的《润化—亚太媒体艺术节》,是国际新媒体元年。随后在2004-2006年期间,张尕做了一系列的新媒体艺术论坛(《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展暨论坛》)。02年的《润化》项目中我作为项目管理人和制作人,在这个项目上我开始接触到像邵志飞(Jeffrey Shaw)和王功新的项目等等。当时Kim就在提 “湿媒体”这一概念,就是带着情感去看新媒体。
那时我从英国回来没几年,参与《润化》的同时我也是藏酷的艺术总监,还在做一个艺术网站(starV)的小主编,之前在“北京伊人文化”我还参与做“喜力节拍音乐节2000”。因为我的兴趣方向特别广泛,所以也常有这种跨界和各种各样的人工作的机会。我协助了英国巴比肯、日本基金会、歌德学院的一些工作,并在2008年之前就实现了非常多的大型的项目。比如说07年王郁洋先生的《人造月》在工体的首展,这个项目是我当时委托他为歌德学院20周年创作的。2005年左右,我是《美丽新世界——当代日本视觉文化》6项目总监,这个项目在北京的几个空间(长征空间、东京画廊、映画廊)中实现,参展的日本艺术家括:池田亮司、押井守、草间弥生、UJINO、渡边豪等等。也就是说,新媒介和跨媒介领域的艺术家,基本都在那个时间,彻底地在中国被呈现。2004年我还作为巡展负责人,协助巴比肯的英国当代独立设计展《沟通》,在中国四个城市做巡回展。当时新媒体艺术史发展的逻辑——是混乱的,它并不完全是某一特定线索下的历史,因为撰写轴心都不太一样。
2008年,我作为总监参与到展览《合成时代》中。张尕是总策展人,范迪安是主席。这也是中国的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的首展。在张尕带领的 “全球扫描”下,各种形式的媒体艺术几乎被一网打尽。
2008年后,我主要在瑞士居住和工作。2014年在高世名的支持下,我们在中国美院做了《和新媒体说再见》系列研讨会。过去的路径,在新媒体艺术发展中有点说不通了,我邀请了奥伦·卡茨(Oron Catts)、ETOY、马克·李(Marc Lee)等人,从生物艺术和金融化等不同领域,去讨论新兴的媒体艺术方向。国内有aaajiao、周姜杉、龙星如等,谈论涵盖 “信息艺术”“社群”等话题。在这一时期,大家是有意识地,在更新新媒体艺术路径。
另外,我想在瑞士艺术家的领域,重新梳理跟媒体艺术相关的线索。在与Roman Signer工作中,7 我们已经有7个美术馆展览——其中6个发生在中国,1个在欧洲。从爆炸物,到超8毫米胶片记录,再到现在的数字化,以及整体呈现作品所采用的技术手段等等,像此类持续发生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是奔着媒体艺术史的研究线索去做的。
2014年前后,作为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CAC)的发起人之一。当时许多工作已从对策展的反思,过渡到了对系统搭建的期待,特别是搭建更好的可循环系统。邵志飞(Jeffrey Shaw)和胡介鸣的两大项目作为开端,已经给机构搭好了结构,并给出了标准。
2021年5月,我在嘉德艺术中心策划了刘嘉颖的一个大型展览《一个小目标》,8 内容涉及了加密艺术相关的几乎所有领域。那时正好是Beeple的NFT创下拍卖记录的一个多月后。整个项目是一个反向工程,交易活动早就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了——这也是新兴媒体艺术旁支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先有了虚拟世界的作品,再有现实中的实在物。
汭:陈小文老师和李振华老师经历的是跨国界跨语言的全球化,那么毕昕,我们这一代是否因为地缘政治的讨论产生了不同的风格?
毕昕(以下简称“毕”):我所工作的机构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CAC)的定位是一个立足在国际背景下的机构。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参展艺术家及项目都与国外有频繁的交流和很强的连接。2020年至2022年,国际交流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其中不仅是展览,驻留项目也受到影响。2020年的学术奖金项目与昆山杜克大学合作,幸运的是,当年的驻留项目获奖者是中国艺术家郭城。但很多其他困境无法自然绕开,除了项目被迫延期外,布展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执行问题。首先,大部分参展艺术家都无法到现场完成作品的搭建,这使我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疫情导致了高额的运输费,有时不得不采取部分本地制作的方式完成作品搭建。这个过程还有一些遗憾,虽然展览的完成最重要的是为了观众,但艺术家缺失了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不同文化语境和空间中与其他作品对话和联系的直观感受,也缺失了去往展览本地进行更丰富、更深入的文化交流的机会。其次,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承担着重负,需要分担一半艺术家的角色:克服时差的困难,提高远程协作能力,与艺术家一起将作品在本地完成。
关于我的个人经历,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可能是我的第一个相关实践。2016年之后我来到上海加入CAC,这是我进行媒体艺术研究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开始。2017年至2019年,在维护机构运营的同时,我的策划方向从展览转变到了公共活动上,这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公共活动是对展览项目更为完整和深层的解读。我们可以充分展开话题,使观众更好地了解展览想表达的内容。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的研究一直是围绕着探索后人类现实之社会、政治、经济与环境寓意相关的媒体艺术实践而展开的,这包括了近年与技术哲学相关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人类纪、机器生态、非人类/不止于人(more-than-human)等实体的能动性,环境的紧迫性以及科技、自然、社会之间的纠缠状态,等等。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对物质性的新思考也包含在其中。但我觉得上述话题从来都不是崭新的,只是在不同的年代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我们有不同的解读,赋予了它们不同的意义。

近几年,我们每年的项目策划都有非常明晰的方向。2020到2022年的研究方向分别是网络艺术、人工智能与生物媒介(biomedia)。我们想通过去年的展览《缠绕:生物/媒介》(Entangled:bio/media)讨论生物媒介——一种从固有的生物艺术的概念中解放出来的学科。也就是说,将所谓“生物”或“生命”的概念,从一门通过技术手段处理细菌、基因或转基因材料的艺术实践,提升到将人工智能、电子、算法、信息学以及生物介质(biological agent) 视为艺术创作必要条件,探索技术发展到今天所呈现的亲生物性;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拓展我们对生命的理解,以及媒介的能动物质性。我们也以动态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展览:展览分为四章,从去年七月开始,每个月底我们开启一个章节,最终在十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呈现。因此,这个展览也处在一个不断生长的状态,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与观众产生对话。此外,我们也在这个展览中尤其关注亚洲艺术家对于生物媒介这一话题的理解与阐释。
汭:从你们的经验来看,有哪些重要事件、展览是从中国本土价值体系中发展而来的呢?哪些又是受到了西方的策展史上的重要运动所影响?
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06年张尕在世纪坛做的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展。我参与了这个活动,带去了我和康奈尔大学HCI(人机交互)研究团队合作的作品的雏形,也在研讨会上做了发言。
无论是展览还是艺术节,我觉得当时有两种生态:一种就是艺术家自己发起。我记得宋冬跟我说起,他就是在和一批艺术家一起做展览活动时,第一次看到了王功新的《布鲁克林的天空》(1995)。那个时代,大家对这个作品都挺好奇的,宋冬认为它是王功新做的最好的一件——后面的作品都没有超越它。可见当时艺术家群体在一起的那种碰撞。
第二种是比较学院派的展览,往往伴随着国家项目出现。张尕老师第一次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鲁晓波老师在世纪坛合作的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展应该是学校当时一个比较重大的科研项目的结题。这种形式的展览后来其实有很多,例如刚才毕昕谈到的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就是属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策划的。展览由学院参与并给了资金支持。而由学院学科发展而来的展览往往强调学术上的话语权。
因此在做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的时候,我与费俊、靳军还有宋协伟纠结最多的还是学术主题。这个主题不一定要完全根据媒体艺术的发展生态走,它可以是与这个学科相关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话题。2006年首届双年展,我们把主题定位在了“技术伦理”。到了第二届,汪民安提出可以考虑以后生命为主题。第三届双年展,9 我与王乃一策展的时候比较关注生态,把主题定为了“合成生态”,关注点不是特别宏观的政治口号式的东西,而是稍微更细腻和具体一些的,比如围绕生存条件的变化。
李:我所工作的90年代,策展基本都是自发的,很少有对西方系统的引入。大家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到的西方系统,是特别碎片化的。通过引入各个国家的高手,去系统地识别展览史,或媒体艺术发展史的线索。但我们并不太清楚,这些高手是否处于某种全球艺术史的框架中。后来随着工作,我慢慢发现每个地区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虽然大家在技术及同时段内讨论的话题上具有统一性,但在不同地区文化上,它所表现的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最近,我刚在韩国看了Moon & Jeon (文敬媛和全浚皓)做的蛮可爱的展览。10 展览里有 Boston Dynamics(波士顿动力公司)的狗,他们用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为狗添加了一个外置插件来感知碳排放,然后狗根据碳量和人群关系给出反应。现场蛮震撼的,我很羡慕一个集成的智能硬件,能直接介入媒体艺术领域。因为,我们越来越难有这种真正介入的可能性。
可介入性(accessibility)是这两年和朋友讨论最多的。如果你不是依附于一个大型的机构、研究所或大公司的资源,高精尖的艺术工作是有点难的。然而这种情况在早期,是存在的。90年代我自己都能攒电脑,那个时候的电脑是一个更像插件化的解谜过程,太有趣了。那时的可介入性在今天基本上不可能的,比如你不可能把iPhone(苹果手机)拆了然后再组装回去,因为可能会涉及质量保护等多重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科技演进和艺术家的批判性,是有时差的。艺术家需要一定时间去理解科技手段,找到自己对媒介的疑点,再进行创作和放大。我觉得纯技术应用的创作,都可以归于我之前提过的一个“顺媒体”,就是你顺应媒体的情况进行使用。
那所谓的“反媒体”,是如何为媒介本身注入可能性,对它进行改造,甚至破坏,呈现一个新的思维。最近我听了梁文道讲戈达尔,戈达尔的电影其实就属于“反媒体”艺术——它不好看,但会提示你拍摄电影存在的某种真实可能性。
这个问题重点是,讨论东、西方系统的搭建和影响,很早就有策展人提出体制批判,在中国的艺术领域,其实是没有(艺术)体制的,所以谈不上(艺术)体制批判。如果要批判的话,可能会引申到政治(政府)体制,但是绝对没有艺术体制。中国的艺术系统和制度都非常不完善。美术馆是美术馆吗?艺术中心是艺术中心吗? CAC是一个特别标准、特别好的艺术中心,它做到了。但非常多的机构其实都有模糊地带。我也很怀念陈老师说的,大家一起出资奉献的年代,和那时的艺术创造性,因为我觉得最好的时代,就是大家为了理想,不管何种身份,一起去做点事,无所谓是否会留下痕迹。这是一种特别崇高的精神境界。
但得承认,现实中我们被各种系统裹挟,很多新艺术家的作品是在为市场而做,但他们并没有错,因为他们要活下去。他们在不断地注入能量到市场,让系统崩坏,所以我觉得特别好,一切都有这种平衡的点。我很羡慕Jeon和Moon,可以使用Boston Dynamics和韩国一线演艺明星,这太好了;我很羡慕Jordan Wolfson(乔丹·沃尔夫森),他能做 《Female Figure》机器动态的作品;我也很羡慕Jeffrey Shaw老先生一直有巨大的资金。我想说,合理的系统支撑,对艺术的扩张是有意义的。反过来,好的艺术扩张,对整个的社会文化生态的均衡,是有意义的。其实在讨论时,我也试着区分商业和非商业的艺术系统。2013年,我做K11 Shanghai的开幕展时,11 引用了Micheal Naimark(麦克·内马克)的研究报告,就叫《真实、美、自由和金钱》。如果要了解70年代以来的历史,我们需要知道大公司、艺术家和实验室都做了什么。这份报告截止于2004年,我觉得那正好是社群媒体兴起的时候,所以副标题叫 “社群媒体后的艺术”。
以前社群媒体不分东、西方,所谓地区化的中国社交媒体,是之后才出现的。在此前,全球化是一下子到来的。后来社群媒体应规定地出现,和在三四线城市的兴起(快手、抖音等),这些分流文化下的社群关系特别有趣。社群媒体有一个全球主线,但不同的社群环境,有自己的明晰主线和分线,大家讨论的问题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它的顺应或反对方式是类似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将问题嵌套到它的在地文化中进行讨论。
毕: 我想通过CAC的“艺术&科技@”(A&T@)项目来回应这个问题。这个项目的灵感来源于两个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室文化事件:一个是美国西海岸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ACMA)早年做的 A&T项目,另一个是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和艺术家劳森伯(Robert Rauschenberg)于1966年在纽约发起的E.A.T.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尝试将艺术家与智库和技术企业进行配对,使艺术家有机会接触最新的技术发明,以推进艺术生态的多样化发展。鉴于这样丰富的跨学科实践传统,我们也在国内开启了A&T@项目,希望建立起一种合作机制,在国内将艺术家与工程师及技术公司进行配对,颠覆技术的惯常使用思维,也探索艺术实践与批评的新可能性。
A&T@项目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周期的开拓与实验。这个项目具有一定的研究性质,所以每个版本的筹备时间都很长,大约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所以事实上,我们大概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三个版本的合作。这三个版本分别与三位个人风格成熟且惯用传统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合作——刘小东、颜磊和尹秀珍。这个项目不仅打破艺术家原本熟悉的语言,改变了技术应用的惯常逻辑,同时也考验了不同领域的机构与个人共同协作的能力。
就像振华老师所说,以前大家可以自发去做一些实验性的实践,但现在技术的门槛不断提升,所以机构应该有使命为艺术家去创造一些途径来接触这些技术,并组织不同合作方交流、碰撞实验并共同协作。
汭:中国的数字艺术社群都分布在哪呢?现在数字艺术展览的观众、读者、讨论人群和收藏人群的人口组成是怎样的呢?
陈:我们常开玩笑说,这些艺术科技展览是网红展,但从好的角度来看,这说明展览更面向大众了。
早期是电子艺术,可能还像李振华老师所说的那样是不accessible(可介入)的,后来数字媒体成为了比较大众化的媒介,比较尴尬的是一开始老百姓还是普遍表示看不懂。但这几年的艺术科技展览,大家都很愿意看。当然,观众在社交媒体上的推广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简单来说,数字艺术展览的观众年龄跨度变大了,参观的人群更多元了。
李:我接着陈老师提到的网红展说。我2013年在K11做的其实就是一个超级网红展,当时的观众量达到了60万。是什么促成了这个网红展呢?是不是我为了观众做了妥协?其实并没有。实际上这种聚集,跟城市规划及人群关系有直接的联动。上海K11商城里的这个项目,底下就是地铁站,而且地点就位于淮海路上,这就又回到了 “可介入性”的线索。所以,我们可能在工作方式上,并没有太大变化,我一直坚持有一定艺术倾向和实验性方向的媒体艺术工作。
我最近在成都市美术馆展览《小宇宙:科技主导下的情感》。12 我预测到它一定会成为网红展,因为周边环境太好了。这一预测的经验,源于2019年我在苏州博物馆为苏新平做的展览《万物是凝固的》。苏州博物馆每天人流量,至少有6000-7000人。在成都的项目上,我预测人流量也是这么多。在此基础上,我为展览作品预留足够的安全空间,可阅读性和可介入性的线索,从作品的数量和交互性上做减法,塑造更大型的作品,简化展览。这种减法的意义在于,对展览公共性的考虑。


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公立美术馆,必须要照顾到可介入性的问题,同时也有自己的学术考量,但这不表示需要和每个人(观众)做智力的交锋,要与智力对等或至少是在同一线索中思考的人,交锋才有趣。
至于收藏群体,还处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2007年左右,有藏家问我如何播放他所收藏的数字Beta带作品,这说明我们并没有系统地去考虑数字艺术的收藏展示问题。另一个例子是teamLab在深圳的大网红展。我的朋友给这个项目投了很多钱,他最终不但回收了投资还赚了钱。所以在某种情况下讲,我会考虑,艺术尤其是媒体艺术,可不可能是一个经济活动?如果有可能,我们也可以去思考媒体艺术的经济活动中,所构成的社群连接,这对技术和公众教育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在刘嘉颖个展《一个小目标》中,就给其他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叫Top Bidder的NFT平台,用以支持他们在这样一个另辟蹊径的市场环境,进行交易。新媒体是非常激励人的,因为不管是研究机构、学术工作者、收藏者、还是展览机构,其实都要涉及到这个领域。如何更有效地,将新媒体艺术结合社会环境,使它获得更好的循环,我现在都还在思考。
毕:陈老师刚才提到的观众“看不懂”的问题也是我们近期不断思考的问题——如何平衡展览严肃的学术性与对观众友好的阐释。作品描述的再书写、基本概念以及关键词的阐释都是潜在的方法。但同时,我们也要考量作品视觉与文字在展厅的呈现比重,以避免展览过于“科普化”或文献式。
另外,我们一贯会通过公共项目活动的方式,如艺术家分享会(artist talk)、读书会、等形式让观众进一步了解展览策划的概念。2018年之后,我们开启了一个新项目——CAC工作室(CAC Atelier)。这是一个专注于技术上手体验的月度工作坊,每次活动为期一天,以某一种技术议题作为主题,比如学习用HTML、CSS和JavaScript来编写网页、ASCII图像创作,用Max/MSP/Jitter进行可视化音画编程,或者了解自然语言处理等等。往往以理论讲解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呈现。
CAC Atelier会让听起来似乎艰深的技术更具趣味性,大家可能发现其实有些技术早已渗透在我们日常使用里,工作坊的目的是走入熟悉的、简易的终端背后,理解其运作方式,并一起探讨这些技术可能的创造性与可能带来的危机。
学生是CAC非常垂直的、粘合度较高的观众群体。我们与很多院校有合作,也组织过不同院校同学之间的交流。
2022年,我个人的获奖策展项目《飞出个未来:区块链中的时间多重性》在北京现代汽车文化中心展出,这是一个从时间的角度探索区块链技术共识构造、能量转换与诗意的展览。除了展馆固定的观众群体外,我也非常希望这个展览能够吸引更多行业内的实践者来观看、交流与批评。这个展览还设计了很多互动的环节,尽可能以体验的方式让观众了解抽象的概念。同时,这也是一个 “不稳定”展览——全球金融环境的变化与加密数字货币价值的剧烈浮动都可能影响观众体验的方式,这也是我认为这个媒介有趣的地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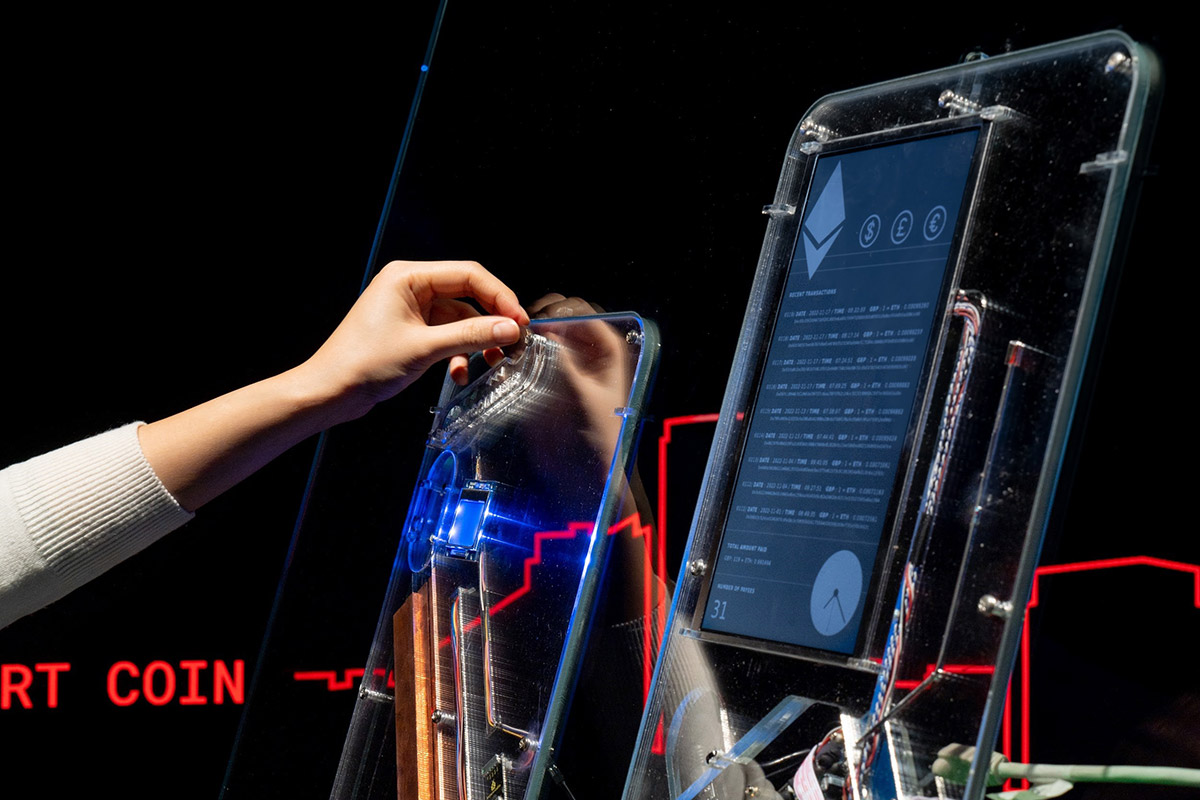
汭:当下流行的思想,如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是如何影响数字策展实践的呢?
陈:无论是学者、老师还是学生,大家对这些热议的主题是有一个全球化的敏感性的。环保、女权、身份的主义都并不是新的东西,从七八十年代到后现代,这些主题在艺术创作中已经很成熟了。那些永久的主题到了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受到新的冲击,就有了新的生命力。这种冲击可能源于社会,例如近两年来发生的社会事件把女权主义提升到了一个焦点的位置,今年我的许多学生的论文都谈到智能、赛博格与女性身体、未来生育等主题。女权主义本身是一个国际性话题,具体落实到中国时,它背后不仅仅是个从文化和人类学角度来谈的个人经验,它还带着特别强烈的社会经验。我觉得这个话题在中国还是挺开放的,并没有受到限制和压制。不过有时当学生和老师讨论涉及女权主义的毕设时,偶尔还是会从一些男教授那里感受一种谨慎又开放的矛盾态度,所以现在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还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陈小文, 现任美国阿尔弗雷德艺术与设计学院(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Alfred University) 终身教授,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客座教授。曾任教于罗特岛设计学院,康奈尔大学。从事绘画、视频和视频装置艺术、互动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的创作与教学。他曾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纽约雪城大学美术馆举办过个人展览。陈小文在2004-2008年参与康奈尔大学HCI科研团队“美术馆观众行为信息可视化科研”,2016年至今与北交大工程学院姚燕安教授团队从事机器人艺术联合科研,2018年至今与中科院广州生物院陈凌教授团队从事生物艺术联合创作。
他曾作为策展人参与策划2016年和2018年的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2022年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2010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国当代版画展》,2010年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纸道-来自美国的纸上的艺术》,2015年在美国威斯康逊大学美术馆举办的《传统与再创-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人物》。他还是出版物《当代数码艺术》的主编。
李振华,1975出生于北京,现工作于苏黎世、柏林和香港。1996年以来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实践主要围绕策展、艺术创作和项目管理。现任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光映现场策展人(2014至今)、瑞士 Prix Pictet 摄影节推荐人。曾担任瑞士保罗克利美术馆夏日学院推荐人、英国巴比肯国际展览 “数字革命“(2014)国际顾问等。
李振华曾主持编撰艺术家个人出版物有《颜磊:我喜欢做的》、《冯梦波:西游记》、《胡介鸣:一分钟的一百年》和《杨福东:离信之雾》。2013年艺术评论以《Text》为书名出版。2015年获得 “艺术权力榜年度策展人奖“、“艺术新闻亚洲艺术贡献奖年度策展人奖”,2016年策划的第三届乌拉尔当代艺术工业双年展(2015)获得俄罗斯创新奖地区当代艺术计划奖。曾于众多国内外机构担任总评委,其中包括:德国转译媒体艺术节(2010)、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现为M+美术馆希克奖2012)、瑞士 Fantoche 动画节(2012)、AAC中国艺术奖(2015-2016)、现代汽车 Blue Prize(2018)等。
毕昕,策展人、研究者。工作、居住于英国曼彻斯特。毕昕的策展实践涉及艺术、分布式技术与当代社会文化/亚文化的交集。她近期的研究关注技术文化中的多重时间性、多变的物质性及分布式能动性,以及非人类实体与人类之间的精神关系。毕昕目前担任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国际项目总监。她也是Hyundai Blue Prize Art+Tech 2022获奖者。
-
阅读原文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数艺网立场转载须知
- 本文由 “数艺网” 授权数艺网发布,已由本站编辑优化排版。 转载请务必在开头或结尾标注 “作者:XXX | 来源:数艺网”,尊重原创及授权权益。 并附上本页链接: 本站部分图文取自网络,如涉及侵权问题,欢迎通过微信 ID:d-arts-cn 告知。我们会立即核实并及时处理,感谢您的理解与监督。














